本帖最后由 lzh13708416 于 2020-6-24 09:31 编辑
人间小事情,天下大诗意 ——读《那些小事情》
凌之鹤 【一】
如书名所示,张稼文《那些小事情》这本散文诗集里所收的短章,其吟咏和关注的,确实皆生活中细小之事物与寻常事务,即使关切眼前风景(或世风),偶然涉及人类的宏大议题,诗人亦刻意执著于往小处着眼,从微不足道的地方轻轻荡开一笔。看起来,这些诗作端然是一个时代旁观者的轻声絮语。它庶几体现了张稼文一贯低调朴素却令人着迷的雅致文风,也准确地表达和诠释了他明朗质朴却格外热忱炽烈的诗观或生活观:身心健康,热爱生活。 平凡寡淡的人生,鲜有大事,多的是扑面而来的芝麻小事。最美情僧仓央嘉措诗云:“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不是闲事?”然而,令人耸然无奈的悖论是——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过于宏大过于抽象的东西端然太多。谓予不信,不妨回望一下我们周遭的小人物,有哪家的世俗生活不为伟大而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裹挟?有几个人不被暗流涌动的物欲和纷繁复杂的世事冲击?想想吧,即使那些仍然挣扎于生活泥沼的浪漫青年,一开口也是豪气干云的“诗和远方”。就连某些人只想赚一个亿的小目标,也令平凡如我辈者震惊。反观今日之文艺界,自负的文化英雄们无不激情燃烧,各路大师、八方文侠,动辄往“大处”挤,朝“高处”爬,言必称大制作、大手笔、大历史,一切文艺创作——小说、诗歌、散文、音乐、电影甚至绘画,都唯大是瞻,都冲着各种世界级奖项发力……我难免奇怪,难道这些龙蛇混杂的大腕大鳄大师们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道所有大事件都是从无数小事情发端?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美丽的蝴蝶翅膀下还隐藏着飓风的影子呢。 说大了,回到《小事情》:且看是书文艺范十足的封面:草绿色打底,如一块绿绒餐布,更像一片柔软的草坪,草坪上放一张蓝色简笔勾画的茶几,几上置写意的茶具,寓招饮闲谈之意;而端然大方颇为惹眼的五个白字书名,仿佛澄澈清波上浮起的五只即将庄重表演诗剧的小天鹅,引人怜爱,令人遐想——读张稼文的散文诗,宜在盛夏或初秋午后的草坪上,就一壶清茶,随清风随意翻阅。 【二】 张稼文的散文诗仿佛吉光片羽,短小,精致,唯美,有趣,好读,耐读。好读,就是能引起特别的阅读兴趣,让读者读之不厌,感觉愉悦;耐读,就是经得起文学审美上的反复推敲琢磨,开卷有益,读之有味,当然也包涵着丰富的精神指向,闪烁着独特的诗学光芒。这些诗章有别于今天流行的那些华丽流畅、讨巧媚俗甚至过度求雅的散文诗,不是大多数读者传统印象中那种刻意押韵、讲究抒情、追求高大上之作,它们天然去雕饰,简洁朴素,混合或体现了多种文学体裁的特质;这些风流蕴藉,张力十足,颇具情节和画面感,寓机智修辞于无形的短诗,有的像闪小说,有的仿佛寓言故事,有的似极短的情景剧或现场新闻报道,有的是哲思隽语,有的神似明清小品,有的浑如独白、梦呓,有的竟宛如素描或速写,——看上去很实在,很舒服,很享受。它们描写的是既是现实与日常,也是感觉和灵思,是我们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生活,它们像耳畔吹过的风声,像眼前飞逝的时光;它们是我们经历的场景、情景和熟悉的风景,也是我们心头不时泛起的微澜、偶然呈现的精神奇观和不期而遇的灵魂舞蹈。 张稼文总是向我们展示或引领读者抵达人生现场,让我们身心俱临其境,而后激起非凡的体会和感受。要而言之,他可以把生活中令人头疼的事故演绎为撼人心魄的精彩故事,他能将无聊无趣的人生写出妙趣横生而意味无穷的诗意。他描绘世情、世相、世态,写的却是我们炎凉飘忽的人情,幽深诡秘的人心,晦暗明灭的人性。这些散珠碎玉似的精美短章,可谓隐忍克制惜字如金,大多只有二三百字,至长不过千字,比如《流星雨之夜》《正人君子》,最短的仅有一行,比如《失眠症患者》《萝卜》。捧读这些标题平淡直白如我们熟悉的油盐酱醋的散文诗,不同的读者大都可以读出自己意中有而语中无的独特意味;哪怕这些诗歌最表层最原始的意思,都能令人心领神会,或莞尔或悲伤,或豁然或深思。这些优美恬静的文字里弥漫着难以言表的淡淡的忧伤,浮动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忧思,偶然也会忽地腾起一道青烟白云,掠过一丝魔幻气息。世间浮华多虚无,人事沧桑少参悟,心里话欲与人言,却总是欲说还休。回头月在高天,可惜身边没一知己。 抛开所谓后现代主义论调,张稼文的散文诗颇接地气,具有鲜活的时代特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们像清晨草尖上晶莹的露珠,虽小,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窃以为这是其诗至为可贵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也是其诗易于打动读者心灵的根源。《那些小事情》精选的散文诗,几乎每一章都允称精品,每一章都能激发或唤醒读者或愉悦或深沉的审美遐思。从选编的时间跨度考察(1981~2019),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这些作品文脉和肌理中发现时代变迁对诗人自身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这些诗作中管窥时代风气之流变。要想在有限的篇幅里详尽地说清这些诗章的美妙及其丰沛的意蕴,殊非易事。为领略张稼文散文诗的艺术魅力,我们且从中随便拈出两章来做一简要解读: 《下吧下吧》(2017年7月12日)这章,单看标题就会让人兴发莫名的情绪:面对成灾的雨季,诗人为什么还要如此请求?完全是一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无奈。诗分三节,第一节交待,持续下了一个月的雨,大暑这日又是成天暴雨。雨水使“马路变为河流,窨井口变泉眼,昆明城变身高原威尼斯”。第二节以假如的口吻披露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新闻事件:“如果前天午夜零点幼儿园教师张春蕊不曾带着她那会跳舞的6岁儿子陈昌硕骑电单车穿行牛街庄新村隧道,那么下吧下吧”。这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个长句,读来让人心碎。肆虐的雨水导致了一桩可怕的灾难。诗人以如此平静的语调表达了自己的悲伤与无奈。如果雨水没有或不会造成死亡的灾难,那就让它下吧下吧!但是没有如果——诗人只好祈求,“这季节,这世界,唯愿漂起来的能成为船筏,沉下去的变为鱼虾”;在最后一节,他斜枝旁逸,竟然匪夷所思地希望,“另,如果云南的每一座山,今年都多长点菌子……下吧下吧”。你看,就是这样一个事件,面对无情的苦雨悲剧,无助的诗人以慈悲情怀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忧伤与祈愿。 《小镇黄昏》(1993年9月5日)庶几可作一部精彩的微电影观。诗人像一个高超的摄影大师,他冷静地摇动、推拉镜头,以蒙太奇手法,将九十年代一个小镇黄昏时分街头忙乱交错却又不失悠闲甜蜜氛围的生活场景(包括世态人情)生动形象地定格在我们眼前:
门槛上削洋芋的妇人削破了手,为父亲打酒的孩子醉倒在街头,玩蛇的独臂人收摊了,收土特产的外省人被缉毒队带走,那个没考上学的姑娘追着一辆货车喊: “等等我——”
这章不到百字的散文诗,以五个大的分镜头,将至少六个或更多的人(妇人、孩子、玩蛇者、外省人、警察、姑娘)在黄昏残阳余晖下的活动情景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仿佛能看到妇人手上流出的鲜血、嗅到孩子嘴角的酒香、想象到在玩蛇人脖项上蠕动的蟒蛇、看着便衣警察带着外省人走远的背影、听到姑娘焦急的呼喊和货车油门的声音。令人惊异的是,这短小的文本之外的巨大留白,足以诱发并满足我们更为辽阔的关于小镇黄昏生活以及活跃其间的那些卑微人物命运的联想:削破了手的妇人是否有人疼爱和关心?那醉倒街头的孩子能否安全回家?玩蛇的独臂人生计如何?收特产的外省人究竟因何被缉毒队带走?那可怜的姑娘是否追上了货车,她意欲何往……
【三】
张稼文是当代文坛的隐修者,他总是淡然置身于那个热闹而势利的文学圈外。他身怀绝技却习惯于安静地独行,在各种名利争执与权势喧嚣中泰然独饮,对于文学江湖中那些明争暗斗拉帮结派的破事不屑一顾。像武林中那些可以寸铁杀人,以筷为剑的高手一样,他偶然出手,不过纸屑飞刀,风起处已瞬间致胜。某种程度上,但他又是沉重、紧张而超脱的思想者,在滚滚红尘中啸傲打拼,面对坚硬的现实世界和意味着无限可能的虚拟空间,他一直在最真实的生活中不懈地探索美好发快意的诗酒人生。你看他那朴实的样子,在豪华写出字楼的电梯间碰到他,如果不是因为戴着近视眼镜,你肯定将他误认为一个进城务工的老农。但你永远不知道他汪洋似海的内心有多潮有多酷。他年轻时候蓄过山羊胡子,人到中年时可以率性地来一个令你惊艳的爱因斯坦头型,也可以光头出入于大雅之堂,闲暇时节俯身侍奉花草,完全一副归去来兮的洒脱。事实上,他的日常生活与我们大多数陷入庸常世俗深渊的谋生者并无二致,每天要面对和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有时难免也会沉沦挣扎于貌似神圣庄重实则无用无益的琐碎事务的泥沼中。我早年曾经冒昧地说过:张稼文是被埋没而值得我们发掘和期待的诗人。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因为他一直在默默地埋头耕耘。当《那些小事情》“意外”地出现,甫一行世,便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关注。我忍不住想说,袋里之锥,总有露头之时;匣中之剑,定有啸傲之日。怀才就像怀孕,迟早总会被人们发现的。 而今,在繁华而繁忙的都市中,张稼文是这样一个率性的赤子诗人,他不安地、警惕甚至挑剔地默默注视着我们置身其间的这个世界:他见蚂蚁无力揎动残翅而恨不能化身为蚁以助其一臂之力(《蚂蚁》),发现绿树生烟结满翠玉珠子般的李子树缠着来历不明的塑料袋碎片时,他轻轻扯下、扔掉(《绿树生烟》);看到天花板旮旯乌云似的蜘蛛网,他居然徒劳地对空向蜘蛛精“喊话”(《喊话》);他有时老夫聊发少年狂,忽发狂“谕”:想做一个放羊看星星的帝王(《谕》);他对于存在的事物怀有一种忍不住的近于冲动的爱,他能从一条受伤的流浪狗身上能感受到人人都有未愈的伤疤(《流浪狗》);他难体会“城管变身小贩”的滑稽与苦楚(《傍晚》),“也注意观察那些来往行人中如天色般忧虑的美妇,也留意到那些瘫坐地上、唱着歌、身边放着一个讨钱币的纸盒的形态丑陋的快乐的人”(《因为我带着伞》)…… 阿多尼斯炫耀说,“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张稼文却决绝坦承,“我的孤独不是一座花园”。他的孤独——在我看来,是流变不居的诡异的日常世事,是变化多端的人间世相和高深莫测的人心。凡我们所忽视或所蔑视的事物,随时都处于细微的变化中。 关于张稼文散文诗的成就及其特质,方文竹的评论颇获吾心。方先生以为,张稼文的散文诗是一种“发明”,是重新命名和刷新表达的另辟蹊径,具有现代性的色彩,他的写作还合谋了传统与现代或先锋,为当代散文诗的典范式写作;其作品突出的一点是:无关而有关——即不动声色地将无关的事物嫁接一起,将现实和梦境有效地融为一体,使其诗作的“灵气和心跳都让你触摸得到”。感叹张稼文“不知道怎样写散文诗”却写出了真正的散文诗,方先生为此断言:“其中的文体启迪极具美学意味甚至暗藏着散文诗的全部密码,并对多年以来散文诗文体之争和当代散文诗的写作现场提供某种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另类映照的价值。”(《张稼文的散文诗·序》) 就诗歌气质而言,我确信,文质彬彬,表象斯文平和,内心却总是涌动着叛逆、戏谑和批判精神的张稼文,诚然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外星人”。这个看起来憨厚可掬实则大智若愚的“外星人”,尽管他曾引用获得首位沙特公民身份的“女性”机器人索菲亚的话不无反讽地说,“我不想成为人类”,但他永远超然地行走在坚实的大地上,他实则向往着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他从容淡定地在人间烟火生活中用心地品味人生苦乐,不断从飞腾的鸡毛蒜皮里发现并揭示忧伤而美好的世界真相——他执著地以小斧子砍大树的精神,用充满个性和灵趣的小小的散文诗写我们周遭鲜活的真正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小事情,最终真诚地写出了令人惊艳的大情怀大气象大境界,写出了天下的大事大势大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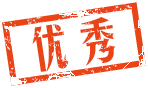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