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罗某人 于 2023-9-18 14:55 编辑
——写给沈从文
无人知道沈从文离世时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闭上眼睛的,也没有沈家哪个人去深究各大报纸在报道沈先生逝世时仅仅用了跟火柴盒大小的一点版面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多少读者对这个消息感到突然、惊讶,懂点文学史的人,多半也是淡淡地咕哝一句:“哦,沈从文死了。”这是在国内,那国外呢?接下来没多久,那个叫马悦然的老外、著名的汉学家,笃定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于沈从文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老马先生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评委之一,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学界和现代文学史的编辑者、教材编写者与读者共同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排挤的沈从文,早在三四十年代就被国外的很多人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作家。马悦然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去询问工作人员,沈从文先生是不是还健在,那官员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人。诺贝尔文学奖有个规定,只给在世的作家颁奖。其实,那个时候沈从文去世也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失去了,对于沈先生来说,无妨,倒是那个官员的回答很说明问题。当然,如果那个官员,乃至更多的官员知道沈先生,在我看来,从某个角度看,是对沈先生人格和文学实绩的侮辱和亵渎。幸好那个使馆的官员不知道沈从文,尽管其人是个文化官员,但这样的人,在国内多如牛毛,戴着文化官员的帽子,往往不是文化人,或者不做文化人的事情,也是常事,包括文学界的装聋作哑,有意无意的冷漠和排斥,也就成为常态了。 沈从文的骨灰最终运回了湘西,安葬在凤凰老城区外一处看起来既不向阳,也不背阴的山坡上,坟前是一块看起来像是随意在山中采来的、形如天茹的石头,上面经常放有一束新鲜野花,不知道是谁从山中摘来,用一根凤凰产的麻线拴住,庄重地放在上面了,但每每又给人随意随然之感。沈从文大抵也是个随意随性的人,其性情虽不至于大大咧咧,对人世物景也不是全然不在乎,但读他的那些人,便觉得他随然而亲和,特像山中草木与花卉,草木处处有,花卉也是,要这样细心采摘,拿来献给沈从文。满以为有花有树有青草,有故乡的声音、色彩和味道,有为数不多的读者和景仰者到来,有日光普照其周身,在月光朗照的晚上,他还能听到远处山崖上或小溪边某痴情男子想念梦中女子的情歌,也看到了翠翠,二老傩送,或者看见夭夭。我有时固执地认为,沈先生可能喜欢夭夭甚于翠翠。但那一切人事只附在文字中,嵌在时间里,剩得沈先生一个人在此,依旧孤独,寂寞,依旧在“乡下人太少了”的叹息中,独自迎对世间的误会,阴间的冷清。至于半坡上黄永玉老顽童写的那句“一个战士若不战死沙场,就将回到故乡”的话,我一直觉得没有完全涵盖沈先生的心性和孤独,甚至有些“歪曲”,尽管作为大画家的黄永玉是沈先生的亲侄子。 童年时代的沈先生调皮,好动,贪玩,常惹事,久之便成了家中长辈的一块心病,尤其是他那个具有苗族血统的母亲,对于他的情形极为担忧和生气。尽管他看起来并不以为然,内心却极为敏感,尽管我们不能以记仇来框定他,但母亲的叹息和责骂,几乎一生都刻在他记忆之中。问题是,年少的人在懵懂中触及到的现实,并非机智到了愚蠢地步的成人所意识的那样,仅仅是表象。不完全是,至少沈从文在凤凰度过的年少时光里,他开始最早地接触了“生命”这个东西,看到了大量的死亡,并使他由当初的好奇,到恐惧,到了不得不思索,乃至善于思索的地步。其实,即便是一个平庸到极限的人,都清楚人必有一死,人生一遭,其实就是为了死亡。沈从文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个道理,即使在童年时代。问题就出在这里。他经常见到枪毙所谓的犯人的场景,开始觉得好玩,枪毙结束后,与顽皮的同伴将一块块石头砸向囚犯的尸体,石头砸在囚犯肚皮上发出的嘭嘭声,使他们获取了极大的欢乐和快感。但经常性看到枪毙、砍杀等致人死亡的现象,使他对“人”便有了某种领会,一些无以明白的想法渐次产生。由此而来,无数疑问也冲口而出,那就是什么样的人,该这么随便地结束他人的生命?又是什么样的人,将生命视着草芥,不值一文?更是什么样的人,可以高高在上,别人的命运成为他们的垫脚石?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这样轻易地将性命拱手交出?更有什么样的人,面对这样的杀杀死死,竟然麻木,或将死视为一种常态?生命,到底是什么?等等,等等。 沈家长辈在沈从文十四岁这年,将他送到了军队。军旅生涯,使少年沈从文开始真正面对世界,也是形成他生命哲学的第一堂人生大课。在这个不长不短的过程中,他不仅差些栽倒在一个同性爱者面前,也得随时提防着小命被某颗铁花生米击中。他用他沈式目力观察着动荡残忍的现实社会,第一次将“生命”作为一种意识放在脑子里。很快,他结束了军队生涯,然后只身到了北京。大半生都呆在北京城中的沈从文,成了一个彻底的独人。孤独是可以吃人的,他孤独难耐到想用金钱去买欢的境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男人,男人有强烈的胜利需求,男人的生命中必须有女人,这很正常。但总的说来,那几年意义非凡的军队生涯,是促使他最终决绝地摆脱他熟悉的乡下人生,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看看的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尽管在当兵的时候,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那时的沈从文,相貌清秀,却始终无法掩饰一个活脱脱的湘西“小蛮子”形象。这一走不打紧,一走就是一生,一走就形成了一个沈从文现象。 很难准确说清楚沈从文为什么要进行文学创作,即便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自以为站得住脚的理由。但那些理由其实并不完全成为文学评论的详实之极的材料(我们大学里这些那些的文艺评论,学术文章,很多材料只不过是拿来为那些毫无建设性和新颖性的观点服务的“死”过不知多少次的东西了,并非是真正的“材料”“本真的历史”等),因为沈从文自己对自己当初的选择都感叹为一种偶然,或者是必然中的偶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孤独,始终是孤独,而且是永远的孤独。沈从文到去世的那一刻,他都在感喟无人了解自己,别人也这么感叹,沈先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连他的妻子张兆和和二儿子虎雏都曾经对记者说过,他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沈从文。张兆和后来又说,直到想了解他,开始了解他,进入他内心的时候,他却早已走远。 不被人了解的沈从文最终成了最为独特的作家,而且作品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但我始终为他不被人了解而感到庆幸万分,在写那本《沈从文研究》的时候,甚至极为反感他经常性地喟叹自己不被人了解,“乡下人太少了”。被文学界冷漠,被极大批量的读者冷漠,被批评家们冷漠,被政客们冷落,文学史至今在骨子里还没完全接纳他,最最新新的人类和上面提到的文化官痞们更不知道他是男还是女,等等,等等,恰恰正是他的价值所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天才和他们的作品,都不是最火暴最热闹最有卖点最好看最有人脉的。他是独一无二的沈从文,不是超女,不是快男,不是浅薄和市侩的文人,不是那些在报刊上发表的毫无新鲜度和忽略内心的、世故圆滑的文章的不入流写手,不是靠文学混口饭吃,或者将文学当成利用的工具的极为下流的人。文学是独立的一个世界,那作家也是独立的,是那个世界的国王(一个曾经在文革时期救助过王蒙的维吾尔族老人,在面对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冒险如此这般的时候,轻描淡写地势说:“一个国家,怎能没有国王和诗人呢?”那么多吃文学专业饭的人,那么多蹲在大学搞文学艺术研究的人,那么多研究“人”的人,写了那么多学术性文章,大抵都达不到这个农民此话的高度,那确实是一件很麻烦很丢人的事情)。既然没有知音,那就活在作品里吧,至少那个可以倾心倾情对话的人,可以在文字里找到。或许沈从文并不这么认为,他赋予文字以生命,就得从生命的层面上找到无数富有真正生命意趣和价值的“乡下人”,因为他被孤独折磨着,被热闹之极的都市蹂躏着。 沈从文内心世界极为丰富,也敏感异常,甚至有些小气,多疑和“怯懦”。因此他也是一个极为爱惜面子的人。尽管他最终放弃了文学,转入古代服饰研究,但他内心深处肯定没有丢弃文学,他一定在某个时辰,极为在意别人对他文学创作的评价。文学界的人只要跟沈从文有交往的,都说他为人极为谦逊,从不自负,也不与人相争。我也相信内心世界丰富的沈从文的修养肯定很高。但这多半是假象。谦虚,并不意味着不争取,隐忍,并不等于不在乎,有时就是虚伪,中国文化人中的很多人不就是这么谦逊着而极端虚伪自私着的么?沈先生唯一无可奈何,无可争取的,是时间。他经常性地哀叹,文字中的心上人几十年之后,还是那么年轻美丽,而爱她们的人,却一天接一天地老去了。除此之外,他没有理由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保持缄默状态。解放后不也是出版过他的作品集吗?他也不是经常性地参与校正稿件的工作吗?他放下了笔,却并没有放弃生命中最伟大的使命——创作。即便他潜心于古代服饰研究,但那些业已成为文物或泥尘的衣服,因为沈从文的心灵和文字,重新活了过来,有人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本“抒情考古学”的书。达到这一步的人不多,懂得文物也是会说话、会唱歌跳舞、会抒情、有伟大的生命意识和艺术之灵动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历史学家如果没有一颗诗意的心,那他们的业绩的成色因为过足而再次使文物第二次“死”去,甚至他们把自己也鼓捣成了“文物”。这一切,包括文物研究工作,之前的文学创作,都不是做了就了了的事情,他仍然需要“知音”,需要“乡下人”,需要赞礼,需要“生命”和信仰。我常想,一个心思既过敏,又缜密的文人,能达到豁达的境界,不大可能。因此,沈从文在放弃写作之前曾经参与了京沪论争,曾经“天真”地以为,伟大的作家及其伟大的作品,有教育一流政治家的功能。显然,这是不能被绝大多数的人接受的,而在政客的眼里,文人根本就不值几个钱。于是,他即便小气起来了,愤怒起来了,到底还是不能在物质世界里奋起一骂。他唯一的命运,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北京的冬天凄冷,干燥。偶尔也参加一下文人们越来越喜欢的大大小小的会议的沈从文,不知道在那样的情形下,是如何让内心温暖和踏实起来的。但每次会议结束,得势的和喜欢热闹的文人们三三两两,嘻嘻哈哈,亲亲热热地结伴而去,唯独沈从文几乎是独自来去,每次都是他独自将会议室的门推开,让寒风将软弱无力的阳光吹进来,将他长长的影子拖在地上,片刻之前还热闹非凡或看起来“好大喜功”的会议室突然显得清冷异常,活像一座墓穴。偶尔,老舍在收拾完东西之后,看见独自一人的沈从文,会逮着他影子喊一声:“从文,等等,我和你一起走。”其实,老舍也是孤独的,他投湖自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孤独和绝望要了他的命,外在的摧残和辱骂,对于他们的死亡来说,档次太低。不知道沈从文是否经常和老舍在一起,更不清楚他在无数文人兴高采烈的时间段里,自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思想的。而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胆怯了,好象他天生的都有一种准确预感时势的超常能力,预判到某些东西即将成为现实。因此,他果断地放弃了文学写作,放弃了参与热闹的大多数活动,几乎放弃了一切。 是的,沈从文的骨子里有怯懦的成分。从追求爱情,到对政治的某种意会,等等,极有可能证明他胆小怕事,怕被整,怕失去工作,怕失去爱和生命。啊,又回到了“生命”这个意义上,那是沈从文的信仰,是他存在的理论基础。他拒绝一些人事,可能是担心那些人事“麻烦”他,干扰他的“生命”,掠夺他的“一切”,破坏他的心情,他对人世间的某些赞美,可以说是对人生折衷、妥协,示弱。他放弃了文学创作,其实是他害怕尘世的争斗,害怕自己成为牺牲品。他十分成功地以这种方式保全了自己。至于文革时期,江青曾经说过她喜欢沈从文的作品,是不是又给生性“胆小”,除了湘西世界美丽之外,其他“地方”都不美好,人事极为不妥的沈从文增添了巨大的压力了呢?他是不是迫于压力,哭泣,彷徨,颤抖,或者做过一些自己都不欢喜的事情呢?他受到过冲击,他在那段人鬼横行的年代里,对生命的认知是不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呢?一个经常性地谦逊,多礼,表现出与世无争样子的人,内心或许跟他们的外在表现形式完全相反。一个害怕失去工作的人,可以将其看成是有奉献精神的人,或者耐不住寂寞的人,或者心地坦荡的人,或者是视劳动为真正光荣的人。但有时,我们又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懦弱胆怯的人,一个害怕孤独、害怕冷清、害怕失去生存之根本的人。我是多么愿意将沈先生看成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完全的没有孤独和寂寞的斗士,一个永不屈服的湘西小蛮子。不,沈先生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被家园丢失的孩子,在多少年之后,终于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了故乡。他害怕喧嚣,因此就独自居住在这既不向阳,也不背阴的山坡上。 这种孤独里有作为乡下人的,尤其是作为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的那点自卑心。我坚信这一点。也可以说,奠定了其伟大文学作品的基调、基本的思想,影响其为人和生活的最大的元素不是其他的,而是自卑。在写《沈从文研究》的时候,我将这点故意拉下了,因为我不能确信那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也不能随意带着揣测的意思就将观点抛出去。但经过这些年来对他作品的反复阅读,再次莅临凤凰,一次次地与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闲聊,一次次地分析建国后沈从文的心路历程,一次次地通过我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的经验去思考沈先生,我不得不很不情愿地以为,自卑,是造成沈先生一系列生存行为和文学创作的最基本元素。尽管他在成为世界级的作家的时候,依旧如此。不幸的是,他没有得到文学史的亲睐,没有被所有的读者首肯,而无数政治运动又使他疑虑重重,担惊受怕,更进一步使他感到与别人与这个社会的隔阂。或许,他在离开人世的前夕,还认为自己不被这个社会接纳,自己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永远充当着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但他又不能再度回归湘西,那个世界变了,已经不是他童年、大美的记忆和浪漫梦中的湘西。同时,作为凡人,他不可能抛弃在大都市里的安逸物质生活,回到已经陌生异常的湘西,他毕竟有他的烟火人间,有世俗的心态。因此,他就像一个完全自由,却不被尘世认可的人一样,自卑而孤独地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将骨灰运回故乡,或许仅仅是一个孩子在凶险的世界里厌倦了、害怕了之后,做出的一个正常而又平常的举动。 那天,某朋友在楼梯口碰到我,说:“沈从文死了,报纸上都登了。” 我怀里还抱着《沈从文小说选》,基本上都是反复读过的篇目。我一边上楼,一边平淡地说:“看到了。” 朋友说:“你要节哀。” 我说:“你很会说话。” 朋友说:“人总归是要死的。” 我点点头,说:“对。” 大学毕业后,我走上了讲台,才发现讲解沈从文,在中国学校的讲台上,尤其是高校的讲台上,是一种极不合时宜的行为,甚至是可笑和“错误”的行为。在培养功利主义者、小人、痞子和饭桶(当然,还是有极少数真正的人人材被培养出来)的高校中,沈从文绝对是一个“木乃伊”,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过气”文人。中国人总爱拿五千年的文明来向世界炫耀,其中炫耀古今大文人,是其最大的嗜好,朗读其诗歌来,唾沫与夸张同飞,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从来就瞧不起文人,不将文人当一回事。 说起来,我的阅读之百分之九十是外国作家作品,余下的那一成阅读,是给予中国文化人的,但也得挑剔过去择过来。于是,沈从文与苏轼李白郭沫若何其芳曹雪芹贾平凹等天才文豪就成为我最持久的阅读和喜爱对象。记得一次在讲解沈从文的小说(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沈从文小说的)时,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将小说写出诗意来,是至高的创作境界!”,并针对沈先生一度钟情于“抽象”,我说:“越接近诗意,就越接近抽象,就更接近美,与神!”(后来这段话成了我发表于《散文诗》杂志上的散文诗《深秋意会》中的一句极为重要的句子)然后我给学生开了一些书目,重点当然是沈从文的作品,我是有意而为之的。 半年后,我就那些书目向学生提问,主要是针对《边城》《长河》来的,但没有一个学生说读过,只有几个学生抽空读了其他几个作家的作品,但大多是读了一半就落下了。 我沉吟半晌,却并不感到沉重,相反,却感觉异常轻松。我说:“你们不必难堪。当今读者群里,绝大部分人不读沈从文的作品,包括其他的世界名著。这种现象,再正常不过了。”更正常不过的是,我自然不清楚现在的很多大学生,究竟是大忙人,还是大盲人。 2009年,我又一次奔赴凤凰,又一次站在沈先生的墓前。那石头上仍然摆放着一束野花。岁月如水,永不停歇地流逝。世间人摩肩接踵地来去,不为内心之虞而忧患,谁都渴望在热闹的物质世界里做物质永远的爱人,唯独眼前这个乡下人,从命运中归来,又回到命运中去,来去都是一个人,不曾赊欠或叩击尘世什么,只有那点诗意的孤独,在成为性灵世界里的一抹光亮与毕生的追忆之后,就将尘世中人,连同尘世本身,决绝地抛弃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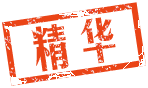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