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四脚匍匐的病榻、垂死的贴紧失血的尘土 摊满金钱、美色、王冠、和那极度穷酸的痉挛 蒙上意志苍白僵冷的床单 放纵死亡的钟声、泯灭黄土悠远的童谣 弥漫安乐的口号与苟且和谐的谎言 毒液从眼窝压迫、两道深深划分贫富的刀痕 病灶在床下复辟、一具层层只剩白骨的腐烂 传说灵魂总是要出窍的 恐怖古老的心跳、假借美化的眼影 散大瞳孔中的黑夜贪婪蚕食的蔓延 沉默吸附在黎明高悬的吊瓶、滴下东方抽搐的鲜血 烧灼无声回光的土地 喷吐故国返照的惊雷 缓缓的滴下了、一株早已枯萎的小草 那瘦骨嶙峋的叶芒上、霜露残泪、颤抖生命的甘泉 面对死亡,传来两种对立的回复 一个浮躁喧嚣、一个沉淀漠然 而当万籁俱寂的最后时刻、能看清的却只有归宿 大地深深的心脏、与苍天空空的血管 换血了、也许能拯救腐朽没落垂死的一己之私 抓住人性的弱点、拿天下来做、一个总设计师的试验 而被淡忘冷落的旋律、唱起来了 一个幽灵在徘徊 没有了信仰而窒息的空气、挣扎起反抗的哀怨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铜臭的谬误把血管中的成份换成了假丑恶 却让真理破碎的心脏坚定、不屈的真善美是永恒的誓言 生命的意义 岂能是是温饱、是交配、是享乐和金钱 生存的真谛 不在行尸走肉的疯狂、酒囊饭袋的喧嚣、而在 共同富裕的豪迈凯歌、与天下大同的壮丽诗篇 血换了、巍巍的红旗飘落 冲上来几个摸着石头的弄潮儿 撤换了思想、撤换了主义 撤换了千百万英烈忠贞的遗愿 甚至用猖獗的房产和黑心的股市,来交易切断文化根基的医院 而最大的绝症是我们无辜孩子们的可怜 在全体教育窒息的太平间里 拥挤着一排排等死无头的躯壳 几代人、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未来、都掉进 血癌杀戮的深渊 幽灵在徘徊、徘徊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朴实渴望小康即安的人们、不是立马就能鉴别 换了身份并不可悲、换了人心才是悲惨 厂长变成了资本家 咱们工人、却变成了机器去为大老板赚钱 村长当上了地主 农民落难、再当牛做马去强拆集体的农田 上上下下的干部都是所谓的公仆 白猫的政策让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先富 老老少少下岗的全是无助的百姓 黑猫的法律却关闭了带动后富的机关 上访的父亲被抓、反抗的兄长获罪 乞讨的阿妹做了敲背小姐、辍学的小弟昏倒在收容所的门前 快咽气的爷爷终于说出、老人家死了、穷人死了、老天死了 乡里、衙里、朝廷里到处横七竖八立着 表叔、房叔、艳照叔、虎狼叔、哪里还有我们的亲人 记住、我死不瞑目、一定要找到、同志 那个被含着泪的母亲喂过奶的伤员 换血是换不去的、一棵沧桑风雨的老树、至死不渝的故乡 那颗植根黄土心灵的信念、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炒作颜色的广告、又回到仰卧的病床上面 直视雾霾的天空纷纷坠落的腐尸 麻木心灵的抢救室里 怵然插满各种血液制品高价怪异的标签 一只通知死亡的手、突然打开房门 撕开天堂与地狱之间、最清贫的善良与最昂贵的欺骗 冥冥中炸响的惊雷、拔掉了救市的插管 急促的冤魂、蹦出最强烈的呐喊 把那几个高雅的小丑打回血泪斑斑的原型吧 同归于尽、万恶的欺世盗名 连同他们侵吞了又无法带走的巨额财富 将它们沤成一桶桶粪水、再还给苏醒复活的绿水青山 滋润我不会再被强拆的菜地、不会再腐败的良田 簇起白灿灿的棉花、叩下沉甸甸的麦穗、以此昭告 千古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志士 与当朝那帮鳄泪落魄的嘴脸 转基因的神话转不了、我黄土根深蒂固的民心 少数先富的理论取代不了、我天下大同的法典 一座天大的火葬场、正在焚烧、换血的病榻 苍白的跳梁小丑、丧魂的张扬末世、刹那的过眼云烟 苍天的血、依旧流入大地的心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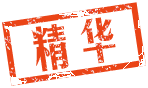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