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诗人的意义
王海云
对写作而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与诗人之间,是存在一种不确定性的,这种不确定性,让诗具有了表演性,或者虚无性的可能,也就是说,一首诗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现实,其实只是现实诗歌的一种关系,而不是诗歌的最后目的。同样,我们所谓的思想呀、观点呀、或者认知呀等等,也不是诗的目的,而只是诗的最后的结果。 因此,一个诗人通过诗歌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同样大于诗人自己对现实的态度。也就是说,诗,只是现实的一种偶然,而不是现实的必然。世界不是唯一的,是变动的、不确定的、充满差异的,甚至你看到的现实,都只是一种表象,甚或假象,是不真实的。 因而,如果我们认同上述看法,或许就能理解,所有的比喻、暗喻、指代等修辞手法,从而使诗歌本身,拉开了我们与具体的现实生活的距离。 在诗歌的背后,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态度、自己的立场。因此,诗歌对于现实,并不是去抗争它,而更多的是辩护,是忽略,是超越,甚至去重构。 在伊沙的新世纪诗典中,我读到过广西桂林一个90后诗人蒋彩云写的一首诗,叫《广寒宫》。伊沙给她的评语是:令人印象深刻,我想说多么美,因为写的是人间,方才这么美,或者说非人间的美是没有意义的,人间无所谓美丑之分,是我们惟一的生存之所。 十六的月亮 翻过了一座小山 便挂在了我的窗前 透过玻璃 我看见 不远处的烂尾楼 已被月光住满 诗人是很有常识的,也是很细心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所以她在开篇点明了“十六的月亮”,这也为后面能清晰地看清“现实”——夜色下的烂尾楼,作了恰如其分的铺垫。结尾,“不远处的烂尾楼,已被月光住满”,回头再看题目“广寒宫”,诗意跃然而出,写的拍案叫绝,出其不意。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现实——“广寒宫”! 在这样的现实中,它之所以产生诗,是因为诗本身的存在。换言之,诗本身之所以高于现实,原因在于诗,是因为语言首先就在那儿,而语言的生成同样源自于诗。而诗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除了因为语言,还因为它们的真实存在。由此,似乎也可以说,诗的无限性,在于语言或者世界的原初性与真实性。 毛毛虫 王海云 一只毛毛虫从地洞里爬出来 顺着洞口边的一根树枝 缓缓爬了上去 我拿起另一根树枝 放在毛毛虫的前头 等毛毛虫爬上我手里的树枝 我将树枝倒过来,插在洞口 毛毛虫顺着我倒插的树枝 又缓缓爬回了洞里 对于《毛毛虫》这首诗,诗人徐一川是这样点评的:这首作品看起来语言朴素平实,无雕琢无修饰,只是透过一个逗弄毛毛虫的小细节,简简单单地叙述这么一个过程。但只要多读两遍,想来是可读出一些领悟的,诗人视角向下,经由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细致入微地观察,完全客观地呈现,很容易产生一种莫名的代入心理。毛毛虫就是普罗大众,且还不仅仅只有毛毛虫,或还有小蚂蚁、小飞蛾,以及无数不知名的生灵……其渺小、微弱的生命、低等的生存位置与态势,往往只能被愚弄欺骗、被牵引、被掌控,而无知无觉。这源于物种之间力量的不对等,能量的悬殊,这是生物发展进程中优胜劣汰的一个体现,而若类比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作品通过简单的场景描述,将一些只可意会的东西传递了出来。 我写这首诗的初衷,就是想借毛毛虫,来表达一种现实生存的“无方向”,我拿起的那根棍子,就是一种法则,一种我们逃避不掉的现实,也可以说是一种被人操纵的游戏,我们被一种游戏牵引着,懵懵懂懂地前行,永远走不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2022年11月29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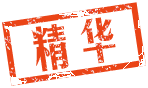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