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浅谈诗词之美(转)
---网络
摘 要
诗词是一种艺术,它饱含了人世间的种种情思。读一首好诗,思想情感会随之跌宕起伏,或激昂慷慨,或流涕唏嘘,或怡然自乐,或笑逐颜开。无论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1]的含蓄之美,还是”犹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无论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的空灵之美,还是“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司空图《诗品》)的充实之美,都能让人暂时忘却自我而扮演着作品里的角色,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也获得美的享受,从而由一般的人生境界向审美境界生成。因此,对中国古代诗词审美的研究,不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对五千年华夏之美的追求。
关键词:诗词;审美;含蓄与朦胧;空灵与充实
前 言
诗词犹如陈年老酒,因历经几岁月的沉淀而醇香诱人。同时在诗词鉴赏中获得的美感经验,又是每个鉴赏者独一无二的实践体验而,这种美的享受让心灵得以净化,让人的审美追求得以提高,故而可以说这种审美境界是一个意义或价值的生成过程,又是一个意蕴的生成过程,是人的精神境界的诞生和扩展。对此本文拟从诗词的含蓄与朦胧,空灵与充实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 含蓄与朦胧
含蓄与朦胧是中国古诗词的重要特征,讲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留有余味儿,通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并给人以无尽的美的享受。
1.含蓄美
中国诗词向以含蓄为尚,而含蓄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审美形态,同时诗贵含蓄是古代诗人和评论家们根据百年来的诗歌创作实践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理论,也是人们对诗歌鉴赏和审美体验所提出的要求。含蓄之诗会给读者留有想象的余地,从而才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才能产生“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钟嵘《诗品》)的艺术效果。袁子才在《随园诗话》中也说到:“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可见含蓄之可贵。
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含蓄美的论述也早已出现。例如《周易·系词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便包含着文学对含蓄美的最早追求。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说:“文以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隐以复议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2]即是对含蓄之美含义的论述。“隐”即“文外之重旨”,即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黑格尔也曾指出“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指引到它本身之外”。[3]可谓“浓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足见诗词含蓄深厚的可贵。而一首好诗多半是用“一叶落而知秋”的手法表现,于尘微中见大千,纳须弥于芥子,让人有过目不忘之感。例如唐人李端的《闺情》: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
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鹊喜声。
这首短诗可以说是通篇口语,通俗易懂,但却没有让人有一览无余的感觉。恰恰相反,它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十分含蓄蕴藉。全诗用形象化的手法,将深闺之情融汇于具体生动的形象之中,意境深远而优美。
读这首诗,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鲜明生动的女子形象。在一个星月皎洁的夜晚,这个女子,急切盼着天明。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次次望着窗外,在期待着什么,等待着什么。直到月亮落下,星辰隐退,天都要亮了,而闺房里的灯还在亮着,她却再也无法入睡。她不禁披衣而起,迫不及待的向门前张望,却失望而归,仿佛连喜鹊的叫声也恼恨起来。短短四句诗,将这位女子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
然而,上述不过是外在表象。作为读者自然会问,这位女子的闺情到底是什么?她在期待什么?等候什么?是什么让她彻夜难眠?……这也就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诗中的女子许是一个独守空房的少妇,在盼着丈夫归来;许是一个怀春少女,在等待着心上人早日拖媒体亲……而这一切都是意在言外。可以说诗人一方面使得女子“披衣更向门前望”的瞬间得以永恒,另一方面也使变动不居的事物在女子转身回落这一点永远停顿下来,凝固而静止。可见“文本不是因为再现而是因为它包孕之前、之后、对立或互补状态而具有意义”[4]。这与“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作只选取“竹喧”“莲动”这一瞬间入诗,但让读者联想到的场景却包孕了无限丰富的内容,也正因此,我们才从中获得鉴赏体验的美感,仿佛我们本身就是诗中之人。
再如金昌绪的《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该诗也是通俗易懂,没什么艰难晦涩的字句,也没什么典故,但却蕴藏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诗中同样是写一个女子,但却不同于《闺情》里的女主人公。前者是夜不能寐,企盼天明;后者是深恐天明,美梦难续。该诗首句“打起黄莺儿”给人以突兀感,既非直接抒情,也非写景,而是一个假想动作。女主人公想把黄莺打跑,她不想让黄莺的啼叫惊扰了自己的美梦,以至于让她无法在梦里到达辽西,去见她远戍边塞的丈夫。诗的内容层层深入,感情步步深化,扣人心弦,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
可以说《春怨》以刻画人物心理活动为主,但作者并不是静止地去描写,而是选择“打起黄莺儿”这个典型细节将其层层揭示出来。我们知道,辽西在辽河西部一带,唐朝统治者曾多次东征高丽,于是辽西一带常戍重兵。可见诗中女子的丈夫远戍辽西,多半是去从军打仗,九死一生。“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是唐代现实生活中千万对夫妇悲惨遭遇的共同写照。但作者并没有直接写生离死别,也没有赤裸裸地抒发少妇的怨尤,而是从少妇的内心出发,抓住她期盼能梦游辽西同丈夫相会的心理活动,含蓄地表达出她内心缠绵委婉的感情。同时,由这种儿女之情我们又能感受到此诗的现实意义,即对战争以及穷兵黩武的统治者的斥责。这也就是所谓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正如大师作画,真正的高手在作“深山藏古寺”这一作品时,不是简单的画座山和庙,而是只画和尚提水这一独特侧面。
由此观之,“含蓄对诗人而言意味着在文本中艺术地构建起开放性的召唤结构,就品诗者而言则意味着艺术审美的深层参与。由于诗中的思想内涵没有表面化和简单化,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就为品诗者作多层次角度挖掘索解丰富其意蕴提供了可能”。[5]
正如法国诗人马拉美所说:“诗只有说到七分,其余三分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分享创作的愉快,才能了解诗的真味”[6]。此处的真味便是中国古诗词的蕴藉含蓄之美。这种含蓄之美是诗人对诗歌的领略体悟,更是对生存本体的一种生命体悟。
2.朦胧美
诗贵含蓄,但含蓄并非朦胧。所谓朦胧,应如隔雾看花,可望而不可及。老子曾说:“道之为物,惟恍为忽。忽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7]而这种恍惚的境界,也正是朦胧之境界,不可明言,却可心融神化。也就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在朦胧的境界中,我们能感受到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在恍惚的意象之中我们又能感受到那种可望而又未曾置于眉睫的美的存在。
而我国古代推崇朦胧的思想源远流长。在上述老子提出“妙在恍惚”后,对诗词意境朦胧性历代文化也曾论及。如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道:“妙在含糊”,汤显祖在他的《如兰一集序》中也说“以若有若无为美”,而叶燮对古典诗词的朦胧美分析得最为充分,他在《原诗》中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界致微渺,其它托足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决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从而产生一种为古典诗词微妙至极的氛围所感染而又难以尽其所以然的浑茫朦胧的模糊体验。
就发生学角度而言审美认识与其他认识一样,也遵循朦胧(模糊)体验原则,也就是通过个体认识的发生和发展,去探讨认识结构的形成以及整个建筑的过程。从客观上讲,古代诗词的模糊体验是以符号性意象为先决条件的,这些意象在古典诗歌中经过无数不同场合的运用而发展演化成体现某些情感、联想等具有符号意义的材料,运用于不同意义系统中,从而产生出不同的意义。比如“落日”这一意象,日之将落未落总会令人想到依恋,故而李白诗云:“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而日落之后的漫漫长夜则让人有孤独凄清之感,故而秦观诗云:“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种由同一意象产生的不同情感是丰富多义的。而欣赏主体在欣赏中不段建构,不断改变自己,因此在不断变化的欣赏主体面前,古代诗词作为审美对象便有不可穷尽的性质,从而产生模糊体验,形成朦胧美。
这与我国古文所说的“诗无达诂”有着相似之处。语言文字作为诗的载体,诗人诗意的表达便具有更多的容量,故而在诗词的题材、主体、情感、美刺等方面也就形成许多不同的意义系统。而就审美主体而言,在欣赏诗词时还以自身的期待视野来丰富扩充诗的内涵,从而产生诗歌的多义性和朦胧性。而诗词的朦胧性是多义性的更高境界。倘若一首诗或词中所蕴藏的意义系统多余三个,就会在欣赏者的审美心理上构成意义群,从而使得审美主体对诗的内涵产生模糊的、难以捉摸的感觉,继而进入一种酣畅舒适晕美的境界,从而形成审美心理上的朦胧美。例如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诗的每联都有朦胧之感。首联听锦瑟繁弦,思华年往事,怅惘难言。而这九曲情肠则形成了诗的多层次朦胧的内蕴。颔联由庄公梦蝶到杜宇化鸟,视为朦胧之意境。颈联的“泪”与“暖”,“珠”与“月”交织在一起,月似天上明珠,珠如水中明月,形成一个“月”、“珠”、“泪”三者难分难解的朦胧之境。朦胧之景,体现朦胧之情。尾联又将诗人的感情世界作了更深层次的剖析:这种情怀已然不堪回首化为记忆,而当初却是那般让人怅惘迷恋。
诗人托物言情,而读罢此诗,我们无法获悉诗人一往情深所追求的对象到底为何方神圣。诗人自己没有说明也未曾暗示,故而此诗便被历代诗论家称为“锦瑟之谜”。这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朦胧美便跃然于胸。
再如白居易的《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我们读这首诗似乎并不能猜出其中心思想是什么,历代说诗者也没有说清楚,但我们可以透过这层朦胧的薄雾去领略其中的意味儿。诗中的“花”“雾”“云”都是具体鲜明的形象,但透过“花非花,雾非雾”“去似朝云”几句,我们又明明能够看到一个美人,如花般美妙,似雾般轻盈,若朝云般飘忽。可谓来如春梦匆匆,去若朝云无踪。就如同一个不能透视但却让人倾慕的美人,朦朦胧胧。同时也唤起读者丰富的想象,获得无尽的美感享受。
由此而知,诗词的朦胧并非无字之书,也非猜谜卜卦,它是一种想象的美,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识自由流动的美。使人在“真与幻”、“即与离”、“似与不似”之间滋生出一种“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心情。
而任何形式的美,都是主观与客观,物象美与情志美,内容美与形式美的创造性的统一。古人所说的“文外”、“象外”、“味外”便在于含蓄美的创造。这不但倾赖于诗人自身,而且有赖于审美主体凭借自己的审美经验去联想加工,从而体会到“超然象外”的意蕴。在此过程中,因审美主体与诗人的审美经验不同,使得诗词的概括性与蕴藉性转化为欣赏者审美感受的不确定性,即朦胧性。因此,诗词的含蓄美派生了朦胧之美。朦胧与含蓄只有当其适度得体,结合为一,才能获得“内明而外润”的艺术美感,从而澄澈而空明,以达空灵之态。如是谈空灵与充实。
二、 空灵与充实之美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物。”(苏轼《送参廖诗》)而“这“空”并非空虚,空无,而是空灵,是超旷、飘逸。”[8]艺术心灵的诞生是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也就是美学上所谓的“静照”。[9]“静照缘起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这时一点决心,静观万物,万物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又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我想诗词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此吧。
而诗词能站在道德和哲学两旁并能立而无愧,也是因为它根植于时代的技术阶段和社会的政治意识之中,有土腥气,有时代的血肉,并指示着生命的真谛。而对空灵和充实之美,人们又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需求,可以说它是诗词精神的两元。首先谈空灵。
1.空灵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侵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10]使人自身能独立于万物之外,与物象形成距离,自成境界。
在古诗词中,风雨是造成这种距离感的良好条件,雨中烟火迷离的景象如诗境画意。而依靠外物造成的空并不是真谛,关键在于内心的空。司空图《诗品》有云:“艺术的心灵当如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这种精神的淡泊也是诗歌空灵化的基础,例如陶渊明。
陶渊明爱素心人,他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故能冰清玉洁,脱尽尘滓。以《饮酒》为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全诗的宗旨是归复自然,回归到人的真性上来。所以诗的前四句说:“自己的住所虽然建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但却不曾听到车马的喧闹声,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心远地自偏。”此处的心远是对世俗的远离,故而所居之处也变得僻静。
接着,诗人(题名为《饮酒》自然是一位微醺的飘飘然忘乎形骸的诗人)在自己的庭院里随意采摘菊花,偶一抬头,目光恰好与南山相会,悠然自得。而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这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旳乐曲。灵动自如。
进一步而言,陶渊明的哲学观中,自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存在,所以才能具足而自由;人生之所以有缺损,全在于人有着外在的追求。那么陶渊明见南山何物呢?日暮的岚气,若有若无,浮绕于峰际;成群的鸟儿,结伴而飞,归向山林,美若梦境。这种自然运动的表现,因其无意志目的、无外求而平静、充实、完美。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总结:在这自然中领悟到的生命的真谛,刚要将其说出却已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这种静穆与淡远,无疑让人有一种余味不绝、淡化心灵的美感享受,空无一物却又四处皆景。
由此观之,所谓空灵,也并非真正的空,而是由此获得的充实,由心远到真意。我想,也可谓之空灵的充实。如是谈充实。
2.充实
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实化成虚,虚实结合,情感与景物结合,便达到一定的艺术境界。周济论词,空灵之后主张求实。他认为:“实则精力弥满。精力弥满则能赋情独深,冥发妾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啼笑,乡人缘剧喜怒。”[11]由此可以感受到一个内容充实的创作带给我们的感动。
欧阳修诗云:“夜惊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赖客思家。”诗中的情感如水,上面漂浮着景物,以忧郁美丽的基调将几种景致联系了起来,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于是便成就了一首空灵优美的抒情诗。
再如《诗经硕人》:“手如葇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中前五句皆是充实的形象,仿佛“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工笔画,而后两句的白描,又是不可捉摸的笑,可谓之空灵,从而又使前五句活了起来。
勃莱克曾说:“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道灿也说:“天地一东篱,万古一重九”。可见大千世界,泱泱天国,皆是凭借“一花”“一沙”传达出来的。“东篱”对“天地”,“重阳”对“千古”又是以无限表有限,用瞬间表永恒。因此,空灵之“空”与“灵”又是由“实”来表现的。
由此可见,空灵与充实是不可分割的,而诗词的最高境界也是艺术心灵的最高境界,便是由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而后真力弥满则万象在旁,可谓“群簌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兰亭诗》)
综上所述中国古诗词博大精深,我们在它的含蓄与朦胧之中获得了丰富的审美体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它的空灵与充实之中,又体会到境界的至深之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参考文献:
[1]祖保泉:《司空图诗品解说》[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57
[2]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2]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1
[3]王元化.读黑格尔[M]. 南昌:白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132
[4]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3.
[5]方根旺:《论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美》 井冈山学院学报 第29卷 第1期 2008.1
[6]马拉美. 马拉美诗论
[7]老子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
[8]陈世明:《论诗的空灵美》;鉴赏文坛.2008,1
[9] 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原载《观察》第1卷第6期 1946年
[10]、[11]宗白华:《天光云影》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第一版 第115页、118页.
原文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612625148?utm_id=0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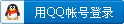

×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