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岸渡口 文/独沐 此岸,醉了。倒在狗尾草旁,遥指着对面的烛光。 彼岸,醒了。站在罂粟花前,冥想着昔日的云霞。 醉了,之后醒了。在无风的树梢上翘首,映像满目沧桑。 醒了,之后又醉。在冰凉的液体中酣睡,梦魇如痴如画。 彼岸有渡口。还在此岸伫立着。默然,一叶扁舟承载着诗人的灵魂飘然远去。 寄托在芦苇丛中的思绪撵着躯体奔波,向着变靠近,再靠近。何日登上渡口的石阶?何日触摸渡口的肌肤?苇荡茫茫,雁过留声。 一花一草,一个世界的眷恋。菩提树下临风,伸手拾取禅音。 彼岸花开了,此岸人回了。用柳枝在沙地上画下一朵莲,十二品的。渡河?超脱?随沙消逝? 期待的曙光,隔了栅栏在彼岸偷偷溜了出来。在水天一色的交接处,璀璨若同那晚桌头的烛光。 梦魂萦绕着雕梁画柱,牵绊在指尖焚烧,那是冰冷的火焰,没有温度。冰寒。冰寒。眼角的泪也凝成了霜花。 河畔的风撩起了鬓角的发丝。伴着柳梢起舞,祭奠的钟声敲响,火烛独明,悄悄地阐述着法轮上的古经。 彼岸,在灵魂与肉体的共振中模糊又清晰。看见一朵似红非红的花朵和若有若无的花蕊搔首摇曳,是召唤?抑或制止? 渡口无舟,彼岸有花。此岸,偏偏独留一道孤单而冷清的背影。静静地,默默地;站着,望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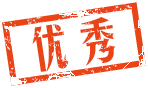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