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雨荷风 于 2015-10-8 10:54 编辑
月夜触膝篇 文/ 山城子(李德贵)
仿佛,你就站在人与物 之间,不是要向大众模糊你的概念。
一些肚子里塞满符号者,喜欢操纵学历为你涂颜。把你整成肥耳朵细眼睛,或弄得小脑袋大乳房。这个说你在外部,那个说你在心间…… 他们用被叫成“美学”的东西打仗。 至今,谁王侯了?谁贼了?事情没完。尴尬得你踌躇:哪里是自己的家园?
正值事闲的季节,我给你盖个透明的小木屋吧!
那条古老的河,那个茵茵绿草的沙洲。但,你不是那位窈窕,也不是岸上的徘徊。但你一定住进去了,并以你的名誉给徘徊与窈窕以不曾有的悦感。或者,给你造一座宫阙,天佬云雾间你散了形骸假寐,窥那些神仙列班而出迎接一个骑着白鹿的人。前来上演亘古豪情、生命激流、大悲大欢。
住进宫阙或小木屋,才可以探寻你,才可以婉约你,才可以缠绵你,才可以不再说:“美 , 我是否认识你?”
其实,我们何曾不相识?你从来都没离我而去。呀呀学语你陪我温馨在爹娘的被筒开放欢乐,
竹马青梅你就在辽西雪化冰消的墙根下,陪着我从悄悄出土的青蒿,领悟春的讯息。
我们相识的历史从来都是紧密地连续。当我长了暗恋的年轮是你甜蜜地羞我,一直羞我到明恋那种幸福的战栗。但你从不说出你的名字。不说出。只让我静静地感觉和谐愉悦或心动情激。
后来你的名字常常裹挟着词素提示我:比如美好、美丽、美艳、美意、美感、美不胜收、美轮美奂等等。可我总是粗心,只能具体着你的家族,想不到抽象你的肝胆,也记不清什么时候从哪个理论家的墨迹里,发现人家动辄就“审”你。待我也学着理论什么的时候就朦胧地请你也坐上高椅子俯视学人家话语口气。直到我不小心跌进一本戴着眼镜的书里,才发现你本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婀娜漂亮,干净娴雅,成为丰衣足食之后人们竞相追逐的期许。
但我不愿让权威胡乱你的内涵,也不喜欢关于羊肥(大)的戏谑。却乐意你被记入《新华字典》的乳义:不过就是“好”与“善”,进入地方,又是“高兴”或“得意”。不过,更多人们鉴于你越来越凸起的消解社会生活和轻松人类生命无可替代的性状与功能,都觉得很必要给你做个成年的大礼——重新名副其实地涵盖你的酮身。你可乐意 听到了吗?美呀 我悄悄地问你。
如果乐意,我已经看到了你淡紫的切线,就沿着天地进入人间。不同于客观实在,也不同于纯粹主观(虽然,古今的大师们这样分别对峙地偏失且偏失得热闹非凡。)
打个比方吧,若喻你为现实的漂亮结果,那么就一定有两个同样漂亮的原因,一如你两朵笑靥泛出的红颜。一朵可感地存在,一朵存在得可感,这样交互的动态才是你漂亮现实的实现。
别撇着你的小嘴不信任我的概括力,还是不认可我抽象的勇敢?我不可能共性不出来一个活生生的你。德国那位大胡子早给了我一样秘传,只要恪守每一个具体,就会抵达幸福共享的彼岸。譬如一朵水仙的洁白静静地客观,譬如一个少女情怀悄悄地纯粹主观,问题是少女的视线偏在此时映入了雅素的水仙。问题是水仙的素雅,偏在此时走进了少女的感官。
走进,是一只小手;映入,是另一只小手。两手环而扣之就建立了一种关系与过程。过程具体在时间里,关系具体在空间里。那朵洁白瞬间飞到少女头上如蝶,飞到一个欲望的落点和窃喜的展现。
美呀,你就这样裹挟着自己的酮体翩然而至,极其自然。如果把具体顺时针过程下去,譬如插花少女她缓步河畔,暖风变得格外轻柔披拂她刘海,河水潺潺如语如诉蜜流她心田。太阳那样明亮潇洒,多像她的相约,一位即刻而来的大男!美呀,这时你会脱口而出,说你已经在太阳河水暖风与少女的感觉之间,享有了协调祥和,享有了愉悦甘甜。美,你已经嚅动了笑靥无疑是由衷得欣然。我的思维已经伸向你了,用温婉的文字携着我的思辨。
你就是那插着水仙花的少女嘛?或者,我就是如约而来的大男。轻轻地喊:美呀美!多么馨香的名字。你说别喊,那不过是个符号般的概念。请径直进入我的内涵。
好的好的,我已迎着你张开的双臂 ——你的发生所必备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客观存在,一个叫主观情感。我由此进入 我轻轻地触摸,我清晰地感觉体验到了两者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及其愉悦情性的过程。
是不是呢,你扑在我的肩膀上落泪激动。霎时,我们就定格得十分圆满。
2009-04-10于上海宋园路
2013-4-5修改于金阳
2014-2-12定稿于观山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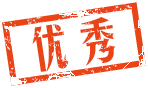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