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农具忆痕(乡土散文诗系列)
文/荷语
引子: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席慕容
@犁头
东岭西岭,南崖北坡,耕夫,耕牛,一副架。
季节更迭,拽耙扶犁,剪影晨曦,剪影午后,剪影斜阳。
一犁犁开春土,一犁犁翻秋闲,犁犁虔诚,犁上一犁阳光照着黄土,犁上一地收成装满谷仓。
“吁吁喔喔!”耕夫在后一声吆喝,耕牛在前奋蹄拉犁。犁头滚滚,泥土翻浪。
转眼日上中天,扶犁的人,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拉犁的牛,喘着粗气,喷着响鼻。
纵然汗珠子摔八瓣,也腌不软他那粗硬的吆喝,挡不住山野桑风吹皱他的额角。
纵然老天赐给他一席舒适的暖炕,也抵不住他在翻阅每一寸饥瘦的黄土中失眠。
他一门心思,犁一季田垄,播一季子种,养一家儿女。
犁头,他的老伙计,一朝与黄土拥吻后,就再也离不开那个犁手那头拉犁的牛。
“父亲”“山野耕夫”是他响亮的名号,他躬身扶犁一辈子,将无数个黑白日子犁翻。
他有一亩三分地,有太阳一般的眼神,扶犁而歌,或许,粗粝的日子也要质感。
当麦子、玉米、高粱被齐刷刷割倒后,他便麻利地扛起犁头,以弯曲的脊梁背负虔诚,亲近黄土,低头扶犁,对着田里曾经丰腴的根致意。
太阳才隆隆滚过他的肩头,寒冬又从前方凛然袭来,他仍然没有抬头,俯首再俯首,用最谦卑最庄重的仪式,扶犁深耕,祭奠根下的黄土
一轮清月,悄然爬上了西山岗。
芦花飞雪。鬓角染霜。燃一炷香,把盏问月:
我该不该将他那挂锈迹斑斑的犁头葬在他熟悉的田头?
我手脚无茧腰生锈,能否像他那样扶犁而歌,将殷实的脚印,一行行植入田垄,刻入黄土?
@镢头
一镢头挖下去,天亮了;再一镢头提起来,解放了。
那是南泥湾开荒的镢头,穿过枪林弹雨,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散发出神性的光芒。
那是兄妹开荒的镢头,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挖出丰衣足食的途径,挖出艰苦朴素的思想。
云和闪电在切磋什么,雨和燕子在排演什么,蝉与杨柳在密谋什么,爹与谷穗在交谈什么……这些很深奥,我不挖掘,我只挖掘简单和快乐。
除了挖掘,我什么也不问。
除了挖掘,我不曾做过别的什么。
后来,我不小心被时间的镰刀割断了把柄,继而又弄丢了那仅剩半截把柄的镢头,而且遍寻不得。
一镢头挖下去,泉水涌了;再一镢头提起来,远山绿了。
总臆想着从虚拟的远山近水中,挖出诗意,挖出灵感,挖出泥土的香,可我至今一无所获。
我累了。忽有麦香从远处隐约飘来。
我起身下楼,循着麦香走向麦田的当儿,发现新割的麦茬中隐约有物闪着神性之光。
@锄头
那一个荷锄背影,定格于岁月的田垅。
那一把锃光瓦亮的锄头,是田野的第一缕晨光。
翻土,松土,一锄一锄的勾勒,一垄一垄的耕耘。
荷锄沉沉,腰身弯成弓,直把对大地的情感一锄一锄融入了自己的血脉和骨头。
累了的时候,他就把锄头平放在田埂上,坐在锄把上歇一歇,抽袋旱烟儿,看看庄稼的长势。
田野归来,顾不上喝口水吧嗒两口烟儿,他就蹲伏在屋檐下,忙着把锄头上的泥土擦拭干净,像一个母亲对待刚出世的婴儿那样细心。或许锄头就是他背负着的责任。
那布满老茧的手,握紧锄把,刨开大地的冻土,给开春的土壤和种子一丢阳光。
那抚摸锄头的手,像是要抓住时间的镰刀。那深邃的目光,像是在挽留温暖的太阳。
黑白更迭,土地把锄头磨损一点点,荷锄的人苍老一点点,田里的禾苗茁壮一点点。
知了,知了。蝉,可劲地知了,知了。可他不觉得自己一直被锄头拉着牵扯着,一点一点把粗粝的生活从田间地头挖出来,又装进了自己编织的箩筐里。
噫!一顶斗笠,一把锄头,谦谦背影,用弯曲的思维亲近黄土,直把滚圆的谷仓填满。
@斧头
记忆中,那一把斧头,很不起眼。
生铁锻造,火炉淬火。平时闲置在庭院角落,它总是默默无闻。
可它又很有灵性,不管给它换上什么材质的手柄,它并不缺少钢火。
将它抡起来,砍下去,能修理旁枝,能砍柴劈柴,能弑杀生灵,能劈旧貌换新颜。
老爷爷说过多少回:斧头本无好坏,关键看能否遇到懂它喜它的手。
搬个小板凳,月亮地上围坐,听老爷爷讲关于那把斧头的故事。
生死关头,再拾起那把利斧,它照样能砍下侵略者的头颅,救民族于危难。
@扁担
“伐木丁丁”,唷唷嗬嗬!挑山号子,穿透山林。
挑过山,挑过水。一根扁担,一担乾坤。
简朴的扁担,“一”字模样,横竖一根筋,横是坚忍的品格,竖是坚韧的脊骨。
窄窄的扁担,一头挂着家庭的希望,一头挂着子女的目光。
短短的扁担,懂得大山子民硬朗肩头的弧度,担着大山子民的长梦。
憨憨的扁担,一头挑着汗水淋漓的喘息和呻吟,一头挑着星星燎原的子种。
弯弯的扁担,闪上山岗,闪下峰岭,闪上斜坡,闪下陡坎,闪上窄桥,闪进一片平野和深湾。
木讷的扁担,挑着木柴的思想,挑出日子的色彩。
笃实的扁担,把晨曦挑进夕阳,把步履挑进笃实,把贫穷挑进过往,把阳光挑进田畴,把福祉挑进谷仓。
直愣愣的扁担,直溜溜的一根,放在肩上,力担千钧,不摧不折。
颤悠悠的扁担,是农民工的扁担,城乡之间一肩挑;是挑山夫的扁担,天地之间一肩挑。
湿漉漉的扁担,挑过素月、风雨、禾苗,挑过陶渊明的东篱菊,挑过归隐诗人陶然的心境。
汗津津的扁担,一步一移地挑走了挡道的王屋太行山。
行走的扁担,一步一挪地走过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出了万水千山只等闲。
心比天高的扁担,劈开了千帆竟舞的古运河,筑高了瑰丽辉煌的皇宫庙宇,挑不尽千万年的时光流转。
深刻在扁担上那种血汗浇淬的纹理,凝结在扁担上那种清贫的操守,是中华龙人一辈辈的衣钵传承。
@耙子
想起耙子,就记起一句俗语:自己的耙子上柴火。
求人不如求己。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小时候,我用木耙子楼柴火;长大后,我用木耙子搂乡土的气息。
@花篓
花篓,与花无关,与斤两有关。
花篓,是爹生前为我编的柳条筐,是他为他眼里那个瘦小的我减负而镂空的心计。
花篓,是我童年的伙伴,我靠她背猪草,背柴火,背诚实。
@镰刀
乡愁是一弯镰刀。
砍柴,割麦,打猪草……
我的黄色童年,是一把锃亮的镰刀收割的光影。
@俱绳
一条俱绳,两只手镰,一季猪草背回家。
一根扁担,两条俱绳,一季粮草担回家。
一条俱绳,一条盼绳,一生希冀拉回家。
@小推车
一把小推车,一个独轮,吱吱扭扭,推啊推,推过炮火硝烟,推向前沿阵地,把无畏拴在车把上,把胆怯碾在辙印里,推出了军民鱼水一家亲,推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序曲。
一把小推车,一个独轮,吱吱呀呀,推啊推,推过土,推过粪,推过四季的风雨,推过四季的谷穗,推过姊妹的心事和嫁妆,推过兄弟的行李和书箱,推过所有苦难和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再也推不动了,就把自己尘封进了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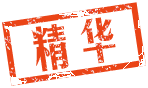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