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雨荷风 于 2015-10-8 09:47 编辑
叙事体散文诗《青春》
文/莫扎特
回头看看你的足迹,它们行走在大地上,翻过了崇山峻岭,越过了险河恶渊……
此刻,暴风雨再次来临,他眺望着前方,誓言要征服俯瞰中的遥远和之外。
没有什么能阻挡前进的步伐,如果心中装着一条路和一双腿。 ——前记
<一> 站在人船来往的海港码头,空气里涤荡着烈日灰烬和海洋咸腥。 轮渡的商船堆垒着延伸至苍茫海天的暮霭里,长短不一的汽笛声回荡着艨艟如梦如幻。 身处其中,迷失自我、单调乏味的热火朝天永不完结。 大城市中心的繁华盛景一刻不止地摇摆,无所顾忌的纵欲遗传自巨轮的媾和。 只冲着昏暗狭窄的天空呐喊出一声声垂死的弱叹息,那正是城市的鼻孔和胸腔。
站在旁边,整个匆忙蠕动的世界宛若一锅被遗弃的粘稠的黑米粥。
高温未退,沸腾依旧,表面和内部爬满了刀枪不入白蚂蚁。 我知道,这里与我无关,而身无分文的我将要跳下去,成为白蚁的美餐, 也必然成为另一个高傲者所鄙夷和同情的看客。
几百个壮汉赤裸着上身在装卸货物,它们堆筑成另一种高山。
排好队,按序上阵,当重担被抛甩上肩膀,全身肌肉即刻绷紧鼓涨。 颤栗抖圆的双腿沉重地向前移动,胫肚的喘息一伸一缩。 不是纤夫,拒绝慢速度。还得挺进一个标准,保持着鹰的队形。 牙齿咬出火花,血液似火舌蔓延进每一身体的角落。 青筋暴涨,汗流浃背。这里是刀山火海,拒绝懦弱,淘汰娇柔。 还有灰尘如浓雾的窒息在氤氲沸腾的风中燎烤,而拼命的苦力容不得带上口罩, 就像迷失沙漠的人,饥渴难忍之时迫不及待要喝下排出的尿。 只披一条白色毛巾穿一条遮当的内裤上战场,干粗活的人没有斯文讲究值得顾虑。
北面,距离码头不远处是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另一条泾渭分明的边界线和大城市相依偎,一端链接着钢筋水泥的腹部。
脏乱狭窄的过道里堆满发酵蚊蛆的物什,腐烂是繁殖指数的胚胎,到处散发令人作呕的臭味。 都是公用之地,少了规章,就只消费不付出。这里没有公德,除了共同的劳累和倒地就睡。 ……习惯了就没有不妥,生活正常地运行着。
<二> 这群码头的搬运工,是新中国经济规划下的践行者,扛着每一栋高楼大厦,游魂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上。 他们都是农民,来自湖南、贵州、四川、云南;他们都是文盲,不识几个大字,更不会写信; 他们都是穷人,种地养不活自己,更养不活家人。他们中最小的刚舞象之年,最大的已年近古稀。 即使被飞速旋转的世界甩掉了很长距离,他们也决不自甘堕落而放弃追逐。
而我也即将成为其中一员。
回想上周找工作的经历,甚是辛酸啊! 卖脑力的,环境好待遇高,受人尊重,生活体面; 卖体力的,环境差待遇低,受人斜视,生活窘迫; 街头卖艺的文艺青年,无人理睬,却也自娱自乐; 唯有乞丐,再无可比,好歹都无所谓,最是悠闲。 赶上时代的浪潮,文盲就是苦力的命。 从明天起,我就得认命。凌晨四点起床,集合上班。 时间快到了,穿过危房和垃圾堆,我们来到码头。
船头高扬着,望向暗黑遥远处稀星几粒,偶有浪花的声音。
灯光被打开,亮彻夜空。码头如浩瀚的夜空,灯火似繁星闪烁。 四周安静极了,海涛压抑不住轻微的叹息。好像一场腥风血雨就要到来,天地绷紧了神经。 而船头开始微微摇晃着,巨大的铁镣发出尖叫的碰撞声。天边透出一条鲜红的光线,鲜血的浪从那里翻滚而来! 另一边,绵延不绝的商船从黑暗之中驶来,饥渴地躺在岸口或在水平面上砸下一个巨形的缺口,催促着我们去喂食或清腹。
如我所见,我正式淹没于这口黑锅中央。
当二百多斤的货包死死地压在我肩膀之上,远比观察和想象来得突然和索命的重量差点将我碾碎。 但我不能掉队,磨破牙埂也要扛出挺立的姿态。是的,习惯就是生活,能让知觉归于不经意。 不经意的我,不经意间在这里干了两年。也于不经意间,改变着我的形体和容颜。 黝黑粗糙的皮肤,暴涨着极不均匀的肌肉和绳索般大小的青筋。我极其厌烦锁骨附近和额头两边的连嚼饭都会一拉一扯的青筋!还有这双奇大无比的绝对握不住粮食的手,它也绝无热度去温暖一个姑娘的冰凉,一层厚实死亡的绝缘质足以打消这个念头。
<三> 每晚七点下班,如加班,要到十一点。如遇暴雨,就不用上班了…… 这些闲暇下来的光阴像毛毛虫,爬满充溢雄性荷尔蒙男人的全身,使年青的心片刻不得安宁。 劳累战胜了睡眠,却是精神空虚的败将。男人们一个个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后来我也去。 往后的日子,我过着一种昏天暗地的生活,直到遇见她,才又回归正轨。
她是新来这里不久的小姐,是个孤儿,被一对湖南夫妇收养。而他们为给唯一的儿子治病,又将她骗卖到此。
一些来自身体深处的情愫和痛使我心声怜惜,竟也陶醉于和她相处的日子。便互许了终生。 带回家,二十岁的我要娶二十一岁的她。但所有人都反对这门婚事。母亲也反对。他们告诉我这个女人的故事: 她是邻村人,单亲。其母亲是闻名十八乡镇的妖婆。母女同一秉性,小肚鸡肠,好吃懒做,水性杨花,骚狸狐气。 她已结过两次婚,喜欢勾引比自己年小的男人。 第一次婚姻,是嫁给一个老实人。和公婆合不来,天天打打闹闹,那男人后来自杀了。 第二次嫁给一个性情刚烈的穷男人。也整天变化着花样折磨老年人,男人用刀架在她脖子上,她才同意离婚。从此,她便消失了,没人再见到她。
……可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并坚信她也一样爱我。
我不信人们口中说的,世人都知村妇无聊就会编造谣言。 我只相信爱人的言语,即使欺骗也无悔无怨。 纵使人们说的都是真的,我也相信她会为我而改过自新。
密语甜言使耳朵高高竖立,巧语花言又将麻醉年轻之心。
爱人的耳语从枕边吹起,好比云雀轻越碧空万里,穿一套彩云装,妩媚投进深情的眼。 沉醉于孽缘的少年啊,为何你看见的全是鲜花,你听见的都是衷肠? 年少不知人生劫数不畏世间埋伏,正迈向悲剧不归途。
<四> 我力排众议,在自我之爱中挂上了新婚的彩礼。 憧憬未来的眼眸在爆竹刹那的烟火上寻觅着永不降温的良辰美景。 曾经的苦难劳累再不会重来,走过新婚之夜,明早就骑上生活的白马!
…唉,可一切都是幻想,如泡沫破灭,人们的警告一一实现。 她对我的家人施以恶言劣行,甚至残暴。极度狭窄的心胸令生活无法前进。 幸好,母亲是个从不言败、坚强智慧的女人。 我是个孝顺的人,即使痴傻至极,也不至于连累母亲。 她是孤儿,二十一岁,无兄妹……我信了。但同时我也信了人们所说的。
把她供在家里,独自忙所有的活儿,我无悔。回家来,煮好饭请她吃,我无怨。但她匪夷所思的性情却让我无法隐忍:只要是女人,无论辈份年龄,只要和我说了话,她都会编造一些故事来。即便是我的母亲! 所有人都憎恨她,同时也不敢再接近我。生活于这样的处境还有什么况味能寻觅? 还有什么光能照进这个牢笼,即使变成水?
母亲一次次决不妥协地战斗着,不让她得寸进尺的疯狂和暴虐得逞。兄妹们加入这场持久战,只有我还常常徘徊。
我对她的爱还未燃烧殆尽,那份人生初见的美好,至今还埋藏在心田。
曾经最艰难的岁月里,我得到了来自她真切而母性的关怀与慰藉。 如美酒令我陶醉又重生的爱意从未消失,于她犯错之时又在心底升起。我要去宽恕和容忍,即便自我伤害。
还记得我用菜刀割腕自尽,不因自我绝望,也不为要把忠诚证明,更不出于一种懦弱的威胁。
人人都晓爱情的伟力能化蛹成蝶,却不知它一样能彻底摧毁人心。 当我望着眼前这个女人,再以没有当初的心跳、陶醉、迷恋、爱意。 从火红的眼睛的云里,一切都已飘远,我的魂灵便于瞬间坠落消散了!
但我没有死去。在通往冥界的尸骨荒野上,但丁的预言一一实现。
我经过一条腐肉尸水的河流,在它的岸边有一座坟墓,那是父亲的坟墓。 一个陌生幽灵爬出来,狠狠地责骂我:“还没有尽孝道,还不懂什么是生活就寻短觅死,是最大的自私; 而无视生命将是最大的原罪;一个家庭里父子都如此懦弱,又将是永恒的耻辱!” 我醒过来了,她已离开。我解除了和她所有关系。
当我回首往事,迷离的光拖着地面上立体的影子从身后到脚下再到身前,我知黎明已到,新的一天就要起航。
而青春从码头的烈火中走出来,站上另一个港口仰望另一重生命的高度。 2013.10(初稿)工大图书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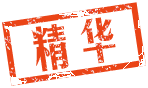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