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柘湖园散帖(组章) 钟楼夕照散帖 诺大的一个园子里,作为拥有至高威仪的建筑,它的存在赋予了这个智识的园囿以最内在的稳定性。它平衡着春夏的繁荣与盛大,也平衡着秋冬的萧条与肃杀。 此刻,在冬日下午并不热烈的阳光照射下,它的大理石立面明暗对比仍然足够鲜明。而在它的四个墙角作为装饰而矗立的十二根立柱,支撑起它的冷峻、正直和理性的高度。它当然应该有一个浑圆的穹顶,不然何以昭示它的智慧和宽容?而穹顶闪烁着金属光泽的避雷针,则最低限度地维持着某种与神祗通灵的可能性——在信仰稀薄的地方,至少时间的神性不容怀疑。 每一次注视它,目光沿着立柱的明暗分界线上升,抵达穹顶,停留数秒,再回到两口钟面黑色的指针(当然不可能同时看到另外两个立面的钟及其黑色指针)。所见的四根黑色指针,几乎毫无差池地缓慢运行,即使是整点也没有被设置钟声,它们默默地强化着时间的神圣性,因而也陡增了整个建筑的崇高感——自觉的人不难为之深受感召而心生敬畏。 钟楼之美是毋庸置疑的。它也只向勇于面对它的人呈现纯粹理性的美,那么静穆,那么悠远,那么轻易就唤醒了他内在的神性自觉,同时也毫不隐讳地唤醒了他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柘湖冬日散帖 柘湖边的草地全部被翻了过来。除了几棵垂柳,原来种在这里的别的树都被移走了,曲径蜿蜒处一下子变得空旷。正值十二月,风过瑟瑟,空旷之外尤见荒凉——以节气论,即使是保持原状,柘湖的冬天本来也免不了几分荒凉。但是计划中这里将被种上樱花,并且前期施工已然开始,翻转的草地显然正静待着新的艳影。 因为可以想见几个月后柘湖春晓的樱花胜景,本来多少有些阴郁的心情也就豁然。虽然描摹不出想象中新的胜景究竟会是什么模样,但是惟其描摹不出,才更引人期待,且任由各自依照自以为是的设想来填补这里短暂的空白。你以为该种早樱的地方,在别人想来却是植上晚樱才相宜;你以为该多种些“初美人”的地方,别人却可能正渴慕着“松月”的重重叠叠。而在瀑布那头,断然是应该种垂枝樱,才能成就谐美的一景。 无论性情中有没有些闲逸之致,只要会幻想,眼前都会依稀出现一幅画,尽管各各不同,不过这正是幻想的妙处。而况柘湖之为名,不但雅极,更透出盈盈古意。人们由眼前局促得无奈的池塘而推想远古柘湖的浩淼,固然是一件徒劳的事,所以本来就只是借其名而名之,对于一所校园来说,这两个字已是一份难得的福泽。不信你试试将这两个汉字轻轻念出来,是不是有一阵水气氤氲,拂面而来? 至于这未来的樱花之盛,应该是被寄予了美好的愿景的。想想明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繁花下的少男少女,必然会萌发他们最初的作诗的冲动吧。 小剧场一瞥散帖 因为濒临柘湖,小剧场当然可以被看作一叶绰约的风荷。偶然从教学楼的北窗居高临下瞥它一眼,它蓝色的顶棚给人以不小的惊艳——寒潮频仍的十二月,它竟犹自荡漾着初夏的风情!它难道不还是一张帆?甚至,不还是一小块海?无论怎么想象与联想,它都该是一个美丽的意象,一个充满了意义的象征。没错,它是一段航程的起点,是一座有远方的青春航站楼。 从校园建筑的布局来看,小剧场算是从规训的秩序中逸出的一个个性音符。如果它是一首歌,它一定是轻快的;如果它是一首诗,它一定是清新的;如果它是一阕舞曲,它一定是自由的。它用轻快的旋律、清新的气息和自由的节拍召唤着那些埋在书堆里的脸庞、蛰伏在题海中的心灵。年轻的脸庞抬起来了,年轻的心跃动起来了,年轻的脚步迈向小剧场的声音,只有春天的潮音略可比拟。 毫无疑问,小剧场是校园里最抒情的一部分,也是最浪漫的一部分。这抒情和浪漫,有着最激动人心最值得铭记的主题——青春。这个舞台很小,小到足以记得你的一段青春舞姿、一段青春颂辞和一段青春誓言。它记得你的十八岁,记得你的毕业典礼,记得你走出剧场大门时矫健的步履。也要想到,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它逃不过是校园里最感伤的一部分——相聚在这里,分离也在这里——它记得你们相拥而泣又破涕为笑的每一个瞬间。 考虑到写下这些文字,不过是在替孜孜不倦于卷帙而无暇旁顾的孩子们作越庖代俎的遐想,不免有些哑然。毕竟,这是他们的青春剧场。 赭红色跑道散帖 让赭红色跑道跑进我的文字里,没有太多理由。温暖,在我想到别的理由之前,最先想到的就只是温暖。这既是一种身体的感觉,也是一种心理的感觉。 冬日,午餐后在校园里踱步,每每不自觉地往操场走,那里有一整块的阳光吸引着我的脚步。沿着四百米赭红色跑道走一圈,仿佛在一个超大的泳池里畅游,而这泳池里装着的并不是水,而是阳光,和冬日里难得的微弱的北风。因为跑道够宽,又富弹性,我甚至不惮于闭目而行,脚步的速度稍减一成,就可细细地感受阳光和小北风打在脸上的微妙感觉。到底是怎样的感觉?是某种自由?或是某种幸福?不能够确定。 但惬意是确定的,确定,又无以言表。 而在风减弱到几乎没有的瞬间,一种浩瀚的温暖在周身流动,让我心生“神与我同在”的莫名感激,就是一瞬间,就在生命的此刻和此刻的生命。生命中真正的闲暇殊为难得,譬如此刻,虽然短促到不过闭目的几秒钟,于身心却能作极有效的修复。瞧,我在,阳光也在,还要怎么样? 至于后来看到在篮架下沸腾的运动男孩,和三三两两横穿过赭红色跑道,雀跃着踏进人造草坪去的女孩,也是平添暖意的美好的生命经验,只是那种暖意有了更加确定的心理内涵。那种来自青春的感染力,仿佛具备了拯救的威力,让我的生命减缓了趋向迟暮的速度——在校园里,赭红色跑道当然是一个极具能量的生命场,既极具引力,又极具辐射力。 “向时光讨来修复身心的一小时 / 在一截时光赐予的富于弹性的跑道上 / 良好的缓冲让我们的脚步变得轻盈 // 快走,或慢跑,都不再是为了追赶时光 / 而是在时光里越来越轻盈,越来越 / 模糊,直到与夜色融为一体 / 直到人世的灯,和星光几乎同时亮起”。我曾作诗如是,以记录彼时漫步在赭红色跑道的特殊心境。那当然是另一种微妙的心境。 百米长廊散帖 这里恐怕是校园中唯一给人以殿堂感觉的地方。白天,当日光透过玻璃顶棚照彻长廊,假如你恰好抬头分享了其中一缕,是否会心生一种崇高感?——虽然校园本来就被赋予了知识和道德的双重崇高,但是长廊给人的崇高感却来自纯粹的空间和人对于空间的神性感应,似乎并不依傍前者。 透过玻璃进入长廊的正午阳光显得柔和,却足够让浮雕墙上浮凸的造型鲜明起来。对于渴望着巨大的审美震撼的人来说,这稍显粗拙的浮雕不足以让他驻足;对于沉陷在日常事务中无暇他顾的人来说,这缺乏色彩的大理石更不足以吸引他吝啬的一瞥。但是假如,你是一个对美并不过分苛求,又乐于忙里偷闲,对周遭平凡事物始终心存善念的人,就一定不会对这日日照面的朴素的美视若无睹。在你匆匆踅身拐出长廊之前,你一定会看似漫不经心地瞥它一眼,内心波澜不惊——巧的是世上恰恰有一种美好,就叫做波澜不惊。 长廊在空间上的特殊规模,即使是一间教堂也未必有其空旷,更不会有其自由。它并不因为高耸而显得肃穆,透明的穹顶让它采纳充足的阳光,开放的空间让它吞吐流动的空气。像这样的冬日,因为风常驻其中而颇显凌冽;不过在春夏秋三季,却是各色花香和树木的气息轮番做着长廊的主人。当然在功用的意义上,孩子们也常常是长廊的主人——歌声与笑声,舞蹈与青春,都常常是长廊的主人。一个偶到的生人可能会敏感于长廊的空旷与单调,而经年从容阐缓于此的人,却时时感觉到这是一个有生命的空间,它甚至是生长着的,并葆有永久的青春特质。 这种生长着的青春特质,在不日就要到来的除旧迎新的夜晚,会招展得更其热烈。当每一层廊柱上的壁灯统统亮起,长廊将迎来一年里最灿烂的时刻,它将盛满快乐和最后的纯真。那些盛不下的,将溢出空间,甚至时间。 柘湖草木散帖(改自旧作) 草木掩映甬道。喜欢校园里这条用花砖拼筑的甬道。短短的甬道,穿过三色杂植的灌木,穿过橘花香里的立夏,再绕过两棵不及碗口粗的银杏树,很快就到了头。和这个美好的节气一样短的拼花甬道,我喜欢在早晨上班时走过它,也喜欢晚上九点半下夜班时走过它。我喜欢它的短、美和芬芳——当年轻的身影健步跑过它的时候,我尤其深刻地感觉到它的短、美和芬芳。 碧桃。当一树碧桃褪尽红红白白,这狭窄的空间才算恢复了秩序。园子里的草木绿得愈益平静、松弛、纯粹。风像一柄油画刀,用柔和的刀法把春意往季节的深处抻匀。 木樨。这个岁数犹敏于花事而讷于人事,几欲自封“花痴”,难免被人诟为“白痴”。这种贻人笑柄的事聪明人决不会干两次。且让人笑去。且属意花开四度的园中木樨。难不成木樨也是痴了?这样的人间也值得她回眸再三而不足,竟回眸再四?木樨有美意呵,人间少“花痴”! 腊梅。三棵腊梅在没有阳光的园子里颤抖,整整三棵腊梅的花骨朵在正月的风里集体下垂,没有一朵抬头,也没有一朵凋零,像走过了锦年的女子,一副唐诗也无力挽救的倦容。它们将一直这样垂首于春寒,直到变成干花,直到不成其形,直到彻底背叛古人的诗情画意。风将带走它们,在某个不为人知的黄昏——没有人用枯涩的笔触记录过它们不再楚楚动人的模样,这首诗,有逃不脱的责任。 白玉兰。五月将尽。一场提前赶到的台风终于偃旗息鼓。甬道和草地上花叶零落,空气里却没有一点衰败气息——灌木丛外,石榴花正热烈登场。仍有白玉兰在独自唱歌,比起初春时她的歌声显得单薄。在越发幽深的舞台上,她像一个戏份不多的配角偶露清影。她有一段清白身世,需孤独地演绎,寂寞地持守,直到季节的舞台更加幽暗。 银杏。在一场注定要到来的冬雨之后,一棵孤独的银杏悉数交出生命的叶绿素。这大自然纯粹的蜕变如此壮怀激烈,几欲力挽狂澜。一棵孤独的银杏不能容忍生命凋敝之时无法逃避的屈辱与丑陋,它用别的生命用来挣扎的时间,向着西风和残照,把血脉中积聚的黄金无声地、一点一点地喊出来——一柄火炬烈燃如斯。这惊心动魄的生命变局成就了它作为一棵银杏的全部美学价值,也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自我救赎,而于我,像银杏一样热烈轮回,像银杏一样,不损失一点美和尊严地枯萎,只能是一种奢望。但我陷于庸常愁怀的灵魂,因这偶然的瞥见而领受烛照,这沉沦中难得的幸运遭际令我心生愧意,又不无欣悦。 两棵银杏。两棵银杏完成了又一次轮回,它们从大地深处取回的绿肯定加了利息。那翘得更高的几根枝丫上招展得一点儿也不见世故的嫩叶,一定是大地馈赠给它们的额外的美。它们的泛青,并不比香椿和盘槐更早一些,在自然的秩序中,它们的谦逊、温良和淡泊总是令人动容。像真正的长兄,在一树三花妖娆莫名的碧桃身边,它们生来内敛和木讷,却也不乏春意盎然。在投向一树繁花的大多数猎艳的目光之外,总也有例外的目光,摩挲着两棵泛青的银杏,静养内心朴拙的诗意;总也有鸟雀停栖在光影斑驳的枝叶间啁啾弄舌,似乎也在吟咏——回到春天的银杏,很美,多美。 碗栀。风中有碗栀之香,我不该抱怨;风中有唾手可得的白瓷、素绢和雪,我不该怀疑;风中有糯软婉媚脆生又年轻的吆喝,我不该怀恨在心。那远了的年轻的声音终究是苍老了吧?因为我也终究是老了。可检点下来,我逐日衰颓的肺腑仍时有沸热之余烬,不肯尽退。内里到底还是深埋着年轻的病根,不肯老去。风里又有碗栀香。只有这碗栀香,只有这白瓷、素绢和六月雪团入我肺腑,凉我沸血,解我鸩毒。 香樟树。一棵把冬雨当作冷水浴耐着性子洗濯枝叶的香樟树,自有耐人寻味的秘密。虽也有和松树一样的遭际,却并不和松树分享不堪承受的溢美之重。即使在冬雨中,它仍然是轻盈的。它抱怨过什么吗?没有任何表征证明它内心曾有怨愤。自然所赐的任一遭际,它似乎都当作了一种不容挥霍的享受。一阵风吹雨过,它瑟瑟瑟瑟瑟瑟瑟地耐心洗濯粘惹在身的尘埃。它内心是悲是喜,不用妄猜,只看它在冬雨里也没有散失掉一点雍容和美,只偏偏欢喜这洗冷水浴的香樟树。 2014.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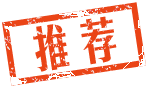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