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雨荷风 于 2015-10-8 10:58 编辑
母亲,是一首诗
文/戴永成
母亲,是一首生命的诗。
生命如歌。母亲如诗。生我是母,养我是母,爱我是母。母亲,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女人。一滴母性的羊水,给了我的生命。一个深邃的子宫,成了我的摇篮。我是母亲身上掉下
来的一块肉,母亲是灵魂最深处的一座碑。母亲活着时候,是我行走的路标。母亲去了天堂,是我灵魂的星光。
母亲,是一首深邃的诗。
母亲的眼睛,是一个博大的海。母爱如海,目光为舟,眼神为帆。母亲用目光载我温暖,用眼神渡我远行。
我沿着母亲的目光,抵达母亲灵魂深处。母性的灵魂,长着童谣、童话、民歌与诗歌的幼芽,我就像一只小小鸟在母亲的怀抱里开始绿色的鸣叫。
母亲,是一首厚重的诗。
母亲的乳房,隆起双乳峰。母性的山,乳泉叮咚。乳汁,从泉眼流出,润泽我水做的童年。那年闹饥荒,母亲吃的是野菜,挤出的是乳汁。母亲一天天骨头变得像芦苇一样清瘦,胸变平了,而乳汁在我的脉管流泻,在我的灵魂中再版。
从此,母亲的乳峰、骨头像大山一样,一直厚重着我的诗歌。
母亲,是一首沧桑的诗。
面对镜子,苍老的是母亲的脸。面对日子,沧桑的是母亲的心。
母亲的脸,一脸皱纹,流成沟壑。岁月之河,从沟壑流过。泪水、心酸、忧愁、苦难、饥荒、寒冷、补丁、伤痕,从母亲的沟壑中流过。
一滴母性的水,从不搁浅。一条母亲河的长度,一日是此岸,一生是彼岸。
母亲,是一首疼痛的诗。
母亲,从草尖上的露珠出发,从睫毛上的霜花出发,从二月里的冰碴出发,从腊月里的雪花出发,走进白昼的白,走进黑夜的黑。一双粗糙的手,结满搓玉米的老茧。那根针,挑亮油灯,母亲把夜色当成补丁为我缝补旧衣。我拉着母亲的手,那根针刺得我心痛。
疼痛,也是路标。母亲把针线带走,真情留下。母亲把疼痛带走,母爱留下。
母亲,是一首人格的诗。
母亲不识字,却懂得“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与“人到无求品自高”的佛语。母亲用人性与佛语来哺育我的灵魂。母亲一生信仰麦子与日子。母亲对我说:“麦子能喂饱肚子,日子能学会做人。”
怀念母亲,让我懂得野菜的力量、善良的分量与人格的重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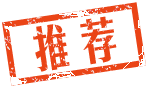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