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郑立 于 2016-9-7 22:42 编辑
奉节:诗韵峡影
夔门
一扇半开巨门,两壁擎天大纛。 门内巴渝,门外荆楚。锁喉八公里,浪吼波喊,鬼愕神惊。 五十米的逼仄,凝墨杜甫赫赫的笔锋:“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众水汇涪万,瞿塘争一门”。 长江,是一枚夺门而过的金钗。 我,也是风中划过的一滴惊悸。 在两岸红叶上,我以猿啼的方式,打捞三峡的遗迹。 在十元人民币的背面,我以澄澈的注目,抚今思昔。 浪遏飞舟的历史,兵家必争的烟尘,改朝换代的响箭,诗心凌云的华章,在奉公守节的草宣之上,灿若云锦。 凿在瞿塘峡壁摩崖题刻的南宋、元、明、清、民国,水渍的历史,尽被雨打风吹去。 夔门天下雄。雄在目光的壮阔,雄在理想的高远,雄在人性的亘古,雄在人心的高度, 锁江铁柱,在白帝城的夔门古象馆,已醉入高峡平湖的涟漪,缄默不语。
白帝城
民谚说:“白帝城内无白帝,白帝庙祭刘先帝。” 白鹤井,收敛了龙气。观星亭,张扬了豪气。夔门,吐出了诗城。我朝辞白帝,也有托付彩云的心思。 吟叹千年的白帝城,推新出陈的孤岛之城,一砖一瓦,都披着历史的褴褛。 公孙述的偏安,刘玄德的遗恨,在明明灭灭的遗迹上,循着情感不同的走向,变换我迥异的眼神。 翘角飞檐上的星象,在诸葛亮的羽扇里潜藏,三国演义,古已分明,今也分明。 在《竹叶碑》,我看三枝翠竹,看三雄结义,看人心冰洁,功功过过写就了历史,不眠的涛声在坎外。 在《凤凰碑》,我读鸟中之王,读花中之王,读树中之王,是是非非浩渺了长江,不泯的烟云在心头。 一座白帝城,满天诗星,满城诗性,满眼诗境。 一城繁花。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真相与历史,让人嗟叹,让人任性,让人心颤。 我在风口浪尖上,夜观星象,批山阅水。
奉节古城
一个梦魇,一条2300年前汨罗江的神鱼,领我泪撒滟滪,鱼复而归。 一声呢喃,一个白帝城刘备托孤的传奇,在三国演义里,草长莺飞。 赤甲晴晖、白盐曙色、瞿塘凝碧、峡门秋月、白帝层峦、草堂遗韵、鱼复澄清、武侯阵图、龙岗矗秀、文峰瑞彩、莲池流芳、滟滪回澜,夔州十二景,涌在我的眉睫上,雨雪纷纷。 在鱼国深处,巴人掩埋的汗血,号子杳杳,长歌嘘唏。
在烟云近处,三峡移民的心音,洪钟大吕,感天撼地。 三峡工程175米水位线上,“奉节人”十二万年来追日逐月的记忆,风驰电掣,灿若星辰。 水深一米是城,水浅一米是诗。水再深一米是古城,水再浅一米是古诗。 诗压住城,城压着诗,诗是城的骨头,城是诗的血肉。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然听见杜甫《登高》苦吟的怅然,触痛着草堂秋风的冰冷。 永安宫、杜公祠碑、鲍超石室、耀奎塔、文峰塔……在残碎、堆积、复制、重建的声音里,唇枪舌战,面红耳赤。 草堂河,梅溪河,谁还在打捞已经沉没的年月? 一城诗韵,叫醒我山高水远的浮想。 一江峡影,重写我此生此世的感动。
天坑地缝
一页袒露的天书,蛊惑世间的痴人。 一枚砸地的天眼,看清大地的谜底。 在小寨天坑。在六百二十六米直径的坑口,我俯身探底,天穹微语,人间阒寂。 在五百五十二米直径的坑底,我坐井观天,天窗似雾,红尘若灯。 在六百六十二米深的绝壁上,在红黄黑相间的岩纹上,我用盘曲的栈道,速写心头的经天纬地: 撒谷溪,勾画洪荒的幻化。迷宫河,容纳红尘的光焰。天下第一坑,斟满了地球的心跳。
天井峡地缝,隐伏十四公里的针线。 时而宽敞如殿堂,丈量我七十余米的心宽。 时而狭窄如门缝,掂量我不足一米的体阔。 玉梭瀑布、犁头湾瀑布、巨象探泉、变幻峰、石观音、双风洞、落水洞、鬼门关、阴阳缝……迷思在一线的针眼,随我穿石破壁。 这是在地球上最窄、最深、最长的嶂谷,虚掩着四十余公里深深浅浅的未知。 人生,需要天坑的指引,需要地缝的剪辑,需要不断地从未知走向未知。 在天坑地缝,我在光秃秃的乱石上,温习伟大的神话,缝补温婉的传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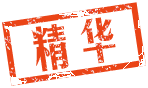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