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角向内(组章)
作者:棠棣
行走尘世,以介词的身份
攀登,攀登,在阳光的簇拥下,呈现自己。
云淡风轻之后,我们都活在自己的影子里,畅饮,冥思,听江流豪放的涛声。然后,把自己交给时光的海,在集体或种属的范畴里,用省略号标注短暂而匆促的生命历程。
起初,我们用时间垒砌自己;后来,我们挖自己的墙角,让时间蚕食自己。如同多米诺骨牌,我们在畅享时光的同时被时光耗尽。
或许,一生仅是一个沙漏,前半生是时光塑形的过程,而后半生是时光剥离的过程。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期间经历了拥有和失去,仅此而已。
拥有。失去。这无从颠覆的命数,任何生命都不得摆脱,包括一片叶子、一朵花、甚至一粒浮尘……
审视万物与自身,行走尘世,我们都是介词,以一个介词的身份,介入然后抽离。
荒芜是时光的必然
荒芜是时光的必然。捕获空隙和疏漏,是所有野性物种的本性,包括低姿态的草。
疯狂的攻陷,从夜晚开始,在我们的睡梦中。
没有喊杀声,没有炮火声,一切行动都是静悄悄地,不动声色地。直到所有的墙垣亭台都被草占据,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和时间一起落荒而逃。
城门已不复存在,我们身后,断壁残垣燃烧着青色的火焰。路也不复存在,和路一起消失的还有记忆。一截枯骨遗弃在绯红的黄昏,任由藤蔓啃噬。
自从我们把背影留下,脚窝里便萋萋着一窝窝徘徊的风,等待收割深夜的月光。
萧瑟从一枚纽扣开始。霜色若有若无,在我们的背后,传出牙齿与金属的斯磨声。
索然。回眸一撇,笑容冷成腊月的苍凉。光秃的树冠上,和月光一起的,是几只正欲飞起的乌鸦。
所有的过往都是曾经
所有的过往都是曾经。当脚步开始,无论有过多少往返,我们一直在走直线。
在生命的维度上,我们一边夯筑,一边拆解。岁月夯筑了生命的厚度,光阴拆解着生命的后路。一朵花,开出生命的香艳,同时凋零着时光的残酷。
我们选择走向山水。而当我们抵达,山水和我们自己都已不是起步前的存在。在山水面前,我们没有太多的兴奋和欣慰,相反,失落的痛楚渐近渐浓。
从一个夜晚到另一个夜晚,我们把马匹和帐篷留下,只带上水和干粮。在抵达之前,我们会选择放慢脚步,可是,夜色却不会有任何顾忌。
倦鸟归兮,日已暮兮,当身影被日光拉长,我们是否会突然顿悟?直到暮色四合,我们苦心构筑的图腾将轰然坍塌。
陌上花开,陌上花谢
陌上花开,不需要想象,生命中的过往常常极其相似。
从学会迈步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注定走不出自己的影子。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行走在别人的影子里。
当我们站直了身体,一个字所诠释的便是永无止境的状态。
从一个概念的确定开始,我们就被象形文字锁定在历史范畴的天空,从白天到夜晚,永远保持着行走的姿态,就像日月山川在原初的认知中被赋形。
当我们给行走中的自己画上句号,也就意味着时光碎片的消逝。
花开自有花落。花早已准备就绪。只是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回到挽起裤腿在清凉的水渠中踩着泥沙行走的昨日。
我们能够让蝴蝶迷失在油菜花的额头。而夕阳中的叶片却在一天天舒展,最终成了某个黄昏我们害怕长大的抑郁。
陌上花开。陌上花谢。归途无觅,我们踩着自己或他人的影子,弥补着生命历程中的蹉跎与裂缝。
黄昏,行进的列车
单程的列车,在出发的同时便开始卸下。卸下喧嚷与聒噪,卸下繁芜与糟杂……直到卸下自己。
我们歌赞黄昏,赞美的是静谧、怀恋与畅想。水边的夕阳、天空的飞鸟、迎面的晚风……
黄昏时分,还在流浪着的身影,内心必是焦虑的。本该出发却被卸下,那是在漂泊的流年,光与影共同抛弃的悲情者。
黄昏,远方尚远。列车在起始站点已完成交接,长长的汽笛声是揪心的痛,蝙蝠优美的弧度划出的是走向寂静的落寞。
如果,这个时刻,还有一棵树在远处站着,勾勒出守望的身影;那么,飘在空中的叶片便是梦的翅膀。当星斗漫天之际,照亮梦境的红烛还在等待一根火柴。迟迟不来的火柴,或许正在列车上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支烟斗。
开一朵花,在雨中
开一朵花,在雨中。
幽寂的雨夜,僻静的角落,让橘色的花瓣绽放孤独。
开放,然后凋零。整个过程,只有雨知晓。
生命,没有必要用来让人欣赏品鉴。在雨中,借雨的清冷感知自己的存在,一朵雨中开放的花便完成了自己。
雨不是观众,只是过客。在风中邂逅,擦肩,然后遗忘。
生命成就于不期然,终结于自然而然。苍茫天地,浩浩时光。所有的大都可以归结为小,而所有的小又可界定为大。一朵花,一朵雨夜绽放的花,在小大之间选择沉默。可以没有名字,可以没有比对,只在雨夜微笑着走过。
橘色的花瓣,不张狂,不冷漠,如一盏灯饱蕴着温暖与爱,爱自己,爱尘世,爱生命中所有的偶遇。
一朵花,因爱而高贵,因爱而内敛,在雨夜,在生命的全部过程,以橘色的火焰呈现出生存的原态。
雪打开尘世的缄默
酒杯已然举起,待雪的眼神映亮炉火。
天地之间,行走的身影淋漓着醉意。那个打马而来的饮者,披一袭风色,让红泥在马蹄声里苏醒。
一场雪,使冬天不再沉默。一场雪,让门户不再紧闭。鸟张开翅膀,水打通凝滞,阳光抹去脸上厚厚的粉底。
树站成傲立的豪客,遥对苍穹,在风中浩歌,让蹉跎的岁月再次蹉跎。山河舞或者不舞,都有酒香在茫茫的白中逸散。
雪中听雪,酒中论酒。雪打开尘世的缄默,让剑歌与豪情柔化成一杯晶莹,满溢暖心的香醇。
天地一色,释放出苍莽中的寥廓。在雪的寒中潜伏着的暖,白亮、舒缓、悠游,借酒香启开泥土封贮的坛,酿一地月色或日影。
我们是被流放的神裔
繁星密布,远处是托起夜空的大河。岸上,篝火已经燃起,隐隐有冰层炸裂的声响。
我们是被流放的神裔,在尘世寻觅远方和归宿。
故乡在远方,前路在脚下。
从来处来,我们没有去处,也不需要去处和怜悯的眼神。
我们围着火堆歌赞春天,在火光中写下朝阳和萌孽的芦芽。
星夜。雪域。我们和风一起,在篝火熄灭之后,向河的源头进发。据说,在河之源,是诸神的居处,那里夜空很低,那里星斗很近……
或许,我们离故乡越来越远,作为神的后裔,在我们开始自己的行动之时,便本能地拉开了与神的距离。
所有的行程都是远方,我们只有在梦中,或者文字照亮的诗行中,才无限地接近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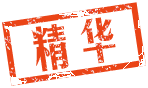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