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乐山船公 于 2019-4-26 17:37 编辑
《诗歌写读杂感》
写这个题目,就是说属于非专业的。俺既非诗歌理论家,也非诗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好者。诗歌对俺而言仅是很小的部分,只是喜欢。所以,俺的杂感,就是一个普通爱好者的写读杂感,仅此而已(交待这些,是不想耽误别人)。 最近读到不少有感觉的诗,闲暇之余,动了写的念头。俺选了一首偏向哲理的和一首偏向抒情的诗歌,略谈诗歌写读的点滴体会。
一、《高处的事物》以自我缩微的姿态膜拜生命
《高处的事物》
太阳是高的 北斗星是高的 它们收割着目光的磁力线---------第一节说遥不可及的高,太阳,北斗星
横梁山是高的 大柏树是高的 它是另一种头颅--------第二节说眼前,说身边高过自己的高,如山和树
奶浆草,斑茅草是高的 镰刀和蜗牛是高的 新生婴儿的啼声是高的------第三节说诗人内心中占据高位的那些物象
我将它们举过头顶-------尾语,对处于高位的生命喻体的一种膜拜姿态
哲理短诗,一般会呈现“悖论”原理,吸引读者品味思考。但也不完全,含有抒情而偏向哲理的诗歌,通常会用递进、分拆、内陷或开合等方式,来呈现哲理趣味。这首《高处的事物》,就是以递进缩微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的尊重。
粗读这首《高处的事物》,会顺着易懂的字面意思溜下来,直到“我”的出场为止,但不会深刻。因为,一般性阅读对尾句“我将它们举过头顶”中的“它们”,是不会深究的。如太阳、北斗星、横梁山和大柏树,你举不举,都在头顶。而那些奶浆草、斑茅草、镰刀、蜗牛和新生婴儿的啼声,你举起,就是一句状态形容。一般性阅读不会去考究这诗中三个“它”是什么关系。就算不统一,好象也不妨碍以实态视角比例来解读全诗。
俺读二遍三遍,又读了春不风度的浅评后,就有深究其理的兴趣。
尾句“我将它们举过头顶”中的“它们”,如果仅指第三节,也是对的。但玩味的在一个“举”字,难倒作者要象举重运动员那样把“它们”举过头顶吗?诗歌在形象处理上往往会借用这些常人熟知的肢体语言,但作者在这里的“举”,显然是表达一种图腾膜拜的肢体形象。即作者以“我”,面对这些“高的”物象形成自我矮化。犹如用一只小蚂蚁的视角,来膜拜高处的圣物一样。而非真实的“举过头顶”。
诗歌有时就象摄像一样,截取一个最好角度形成艺术画面。当作者面向高大的喻体时,以上“举”来反向缩微自己,一幅三角视角场景画面就出来了:最高处是天,中间是山和树,再下来是草及蜗牛等,最低处是“我”,即小小的我、矮化的我。这个三角视角画面,是以“我”为磁场中心的,是以自我崇低的姿态来崇高,反衬那些生命喻体的高大。
从这个角度理解,尾句中的“它们”是泛指全诗中的它,即三个“它”是统一和谐的。第一、二节是赖以生存的环境,三节特指生命核心。既有丰润的牧场、劳动的工具、小动物的慢时光,又有人类生命的传承。这些物象(具象),都是作者心中高贵之物,崇拜之物。为此,以“我”这个微小的磁场视角,以“举”的姿态(举,暗示“我”也是一枚强大的生命体),对生命喻体的仰视和崇高膜拜,构建了这首诗歌的哲学含意:生命的尊重!
二、《内心的褶皱》,来不及愈合的乡愁之痛
《内心的褶皱》
一场花事高悬在枝头 像寻人启事-----------------第一节,把村头的春花比喻成寻人启事,妙! 青春出走多年 村头的那条石板路又矮了几寸 月光深陷其中 洋槐木拐棍戳疼村庄的神经----第二节,村头的老人盼归游子的场景画面 远方 来不及痊愈------------------第三节,远方游子的感应的伤痛
这首是同题诗,俺也写了《内心的褶皱------桃花盛开的德令哈》。俺是借同题写海子,而这首是借同题写乡愁,都属于偏向抒情的诗歌。俺认为这首同题是写得最好的之一,只是版面上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俺写那首,是借用了德令哈的高原、祁连山、荒漠戈壁、巴音河、托素湖、桃花等意象来抒发,其中的意象都可以单独成立。而这首中的每个意象都浑然一体的构建一个熟悉的场景----二月的村头。俺写那首,如果读者对海子不了解,也读不出什么感觉。但这首不一样,是大家最熟悉的,读懂了是极易引起共鸣的。除非被朦胧了,没有找到诗的入口。
一般阅读者的心理思维模式中,作者在场感强的诗歌如有人称代词的,都容易进入。恰好是近似这首一样用喻体假借的诗歌,即隐去“你我他”等人称代词的,不容易进入。这首的入口是在第六句的“洋槐木拐棍”。这个喻体形象并不朦胧,但作者有意把主角出场的顺序后置,与尾句衔接,形成类似倒叙的结构。粗心的阅读,可能会忽略已经出场很久的主角,而一眼带过。
洋槐木拐棍,不是少年儿童的玩具,它只属于行动不方便的老人的助走工具。在这首诗里,也只属于作者极为熟悉的念念不忘的那位老人的拐杖。当老者在孩子的“青春出走多年”之后,渺无音讯之中,已经无数次地走向村头翘望,使得“村头的那条石板路又矮了几寸/月光深陷其中”;每一次的失望叹息,都会用“洋槐木拐棍戳疼村庄的神经”。
作者在首尾处理上极具特色。诗歌首句不说除夕,不说元宵,也不说二月梨花樱花初放的村庄,只说“一场花事高悬在枝头/像寻人启事”。“一场花事”在这首诗歌配境中已经不是自然风光了,而是被安排的,是故意的。这才有“高悬在枝头/像寻人启事”。首句这种代入悬念的叙述语句,精道贴切,令人惊叹。尾句一转,把时空从村头跳向了远方,跳到了被洋槐木拐棍戳疼神经的游子身上----他无论怎样弥补,都“来不及痊愈”。结句这里,那场高悬的“寻人启事”,看似闭合了,但“来不及痊愈”引出的空间极大,余味难收。这种疼痛,不是一般淡淡的乡愁,而是裂骨的,令人脆弱之极。
三、几点体会感悟
1.感悟特点。这两首都应用了叙述句式,选择的具象物象构建的意境都是熟悉的,在结尾突出主旨。全诗没有关联词,且不留痕迹。第二首更没有人称代词,但诗歌喻体的应用高超,如“青春”、“花事”、“洋槐木拐棍”等,代入性很强。
2.领悟佳句。这两首都有神来之笔。第一首的“我将它们举过头顶”,虽然这句并非是首创,但在整首诗歌意图中起到了“骨”的作用。第二首的“洋槐木拐棍戳疼村庄的神经”,支配了整首诗歌的意境。
3.关于神性诗写。神性诗写,是一种诗写状态。神性,并非神异。神性诗写,就是来自于作者对生活高度抽象后的天赐灵感的创作。何中俊老师几乎每日一诗,常出精品,似有神助。至少俺是望尘莫及的。
诗写与读诗,是一种心灵契合。从诗歌论坛大的方面来看,神性诗写,若能遇上神性阅读,是相当愉悦的趣事。许多时候,深度阅析,往往可能拓展作者诗写意图并未抵达的深度和广度。从经验看,现代白话诗歌,跟古诗中明确的诗眼诗骨不同,而是呈现多棱角,留给了不同读者品味的时空。但优秀的白话诗歌,多棱角中肯定有一面,留给了神性阅读者。这二者的契合,正是新诗至今赖以存世的根基。
俺这些杂感,只代表个人水平。这两首可能还有未被挖掘出来的“金矿”。俺水平有限,以写评练笔,抛砖引玉。
(上述杂感纯属个人见解,不当不妥之处请谅解) 乐山船公2019年4月23日晚
附1:何中俊的《高处的事物》和诗者絮语的《内心的褶皱》在版面的出处 (出处: 中国诗歌网)
(出处: 中国诗歌网)
附2:【春不风度浅评】:《高处的事物》,物象抽象化,展开想象! 诗中高处的事物,太阳,北斗星,横梁山,大柏树……一串串意境,又高至低如画延伸,都是高的,这就是诗的独到之处,独特的视野,独特的语言…… 诗中虚实交换:它们收割着目光的磁力线;它是另一种头颅……对高事物的仰望,转换为虚的情景与想像,文字的张力,跨越十分有力,延伸过度的成功自然。 展开想象,延伸诗的纵深:奶浆草,斑茅草是高的/镰刀和蜗牛是高的/新生婴儿的啼声是高的……前两节高处的事物,的确高,这一节的高,出人意料,作者立刻更换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存在,自己有多大?想像空间足够庞大,文字很有重量,自己被压的很矮,仿佛整个世界都是高于自己…… 此处无声胜有声,结尾“我将它们举过头顶……”语言的魅力与张力突然释放,将诗的意境猛然提升,成功之笔,不是自己矮小,而是有力和巨大,超越想像,蚂蚁之神,高处的事物,显现自己的巨大,举起世界,想像奇特新殷,诗很是将空间提升到极致,想像也是,语言的魅力也是,我津津有味细嚼,体会作者创作的历辛与我的快乐,受益匪浅!文字功力深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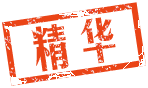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