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哀伤和欢愉:日常的精神之饮
流连光景物候的文字里必有哀伤,也少不了欢愉。 哀伤不值得炫耀,欢愉则更无罪愆。哀伤和欢愉,都是常来常往的故人,岂可厚此而薄彼? 哀伤之来,岂必以浊酒敬之?欢愉之来,复岂必以清茶揖之? 或许,哀伤本身就是浊酒一盅,欢愉本身就是清茶一盏,盛以文字的青瓷或玻璃杯具,是最妥善的相处之道。 譬如,在这立夏不像立夏的莫名时节,去看看盛开的蔷薇,本来是一件欢愉的事——在文字的杯中,这欢愉清入肺腑。 谁想欢愉之莫名,几乎必然地伴生着哀伤之莫名。于是,看蔷薇在风中摇曳这样的事,竟也是哀伤的一种——文字的瓷盏,必须接盛这浑浊,一倾入肠。 因为常来常往,所以俱成平常。流连光景物候的文字,是平常到平庸的。甚而至于是无聊的——却不是百无聊赖。 哀伤和欢愉,俱是日常的精神之饮。特以文字为器,为郑重其事的仪式,是因为所有的哀伤和欢愉,都值得尊重和珍视。 即便它们仅因节令里的一事一物而肇始,如立夏之虚以逶迤,如蔷薇之临风绰约。哪怕都是如许轻的哀伤和如许轻的欢愉。
春天的轻
二月底三月头梅花层层叠叠开着的时候,春天还浅,同时竟也是重的。这几日梅花正落,早开的宫粉和朱砂几乎要落尽,绿萼也经不起踅身而过的女子一碰,一碰就落下一片。 春天是日见深了,却也好像日见轻了。春天还不够深。但越往深处走,似乎就越是轻。 眼看玉兰白在难得的干爽阳光里莹莹发光,在难得的蓝底子天色下剔透玲珑,春天的轻几乎就坐了实。玉兰白,竟是轻轻飞着的春天吗? 眼看樱花和海棠一夜之间蹿出密密麻麻的花苞,不日就将占得她们应有的份额——她们是谁也不会让谁的,谁让就是谁的罪过。 其实几乎要落尽的梅花也没有让过谁,她早早开在春浅时,毕竟还是占了先机。她落没落满南山,最惹游子的惦记。 而樱花的春天是轻的这个事实毋庸置疑——风起时,她就是春天的裙裾。海棠的春天是重的这个事实同样毋庸置疑——雨过时,她是春天的一场病患。 春天到底还是轻了,当我看到樱花和海棠的春天里走过的你,和你鬓边轻扬的白色发缕,就知道春天到底还是轻了。 春天就这么轻轻压在心上,压得心慌慌的。
有谁比一棵香樟更了解诗人
诗人理应允许任何一棵树,或者任何一种树,在春天进入他的诗歌园邸。在秋天同样如此。他的诗歌园邸应该对所有树种无差别开放——阔叶或针叶,乔木或灌木,木本或藤本。 但是在四月的尾声,他却只邀请了一棵香樟——非但没有邀请更多种类的树,而且也没有邀请更多的香樟——进入他的诗歌。当他站在一棵香樟树下,在微雨中细嗅它的花香,他就直接向这棵香樟开放了自己的园囿。 这种邀请或开放,总是带有隐秘的私心的。他期待这棵在四月微雨中完成了蜕变的香樟,能帮助他实现一首朴素诗歌的写作。这首诗歌所需要的蓊郁和芬芳,它都能提供。它像一只胆瓶倒扣在春天里,倒扣在一场微雨中。它趋于圆满和完善的球型树冠,看上去有倾覆的风险,却无需任何担忧。 在春天,四月,他不善于在诗歌中勾兑太多的意义。通常他只需要一棵树,比如出现在街角或园子里的任何一棵香樟。一棵香樟足以撑起一首诗的有限和有效空间——总是有些风险,却不用过分担心。 一棵香樟几乎可以保障一首诗所需的所有朴素品质和基本诚意。虽然另一棵树也能提供大致相同的价值,但是既然有香樟,就把一首诗的命运交给它好了。诗人没什么好纠结的,也不需要后悔——可能没有一棵别的什么树比香樟更了解诗人吧? 它以每一根枝桠和每一张叶子里的香气,证明对一首诗的了解。
雨水散句,或雨花词
三月将尽,人们终究从与雨水的抵牾中醒转,把手伸出伞沿去接迎这来自天国的恩遇。从沁凉触觉中接到的微香,让皮肤也恢复了灵敏嗅觉。 紫叶李在三月的雨水中一度丰腴,现在渐渐走远,留给三月一个瘦削背影。其实她是身怀有孕,要到四月里去静静养心,静静安胎。她袅袅婷婷的背影里有不可自抑的喜悦。 早樱雪白,在雨水中轻轻颤栗。她也是喜悦的吧?以一种轻哀的方式,一种容易让人误会的方式?她几乎对花下走过的人们形成一种覆压,但是因为过于轻柔,难免令人产生恍惚。一种哀喜莫辨的恍惚,雨水起码要负一半责任。 相形之下,同在雨水中颤栗的垂丝海棠要重上几分。她几乎是喜上眉梢的样子,也因此同时有一种显明的哀戚——这哀戚的经验来自过往的一次墓园所遇。这偶然所遇,就此带来某种先入为主而根深蒂固的误解。 边上的西府海棠却是另一副眉目,她不哀不喜,不嗔不怒,神气清爽。有一个时髦的词差不多可以拿来唤她:氧气女孩。要是雨突然停了,她沐在阳光里的那几秒钟,怕是最当得起这时髦的称谓吧? 那么桃花在雨水中的命运呢?说句实话,雨水中的桃花,即便植在柳树边上,也没有人们习常所以为的俗艳。她收拾得干净利落,健健朗朗,绝对对得起这场雨水的眷顾。要紧的是,她也在雨水中怀孕,所以足可消除一切庸俗的、刻意的误解。 梨花也在雨水中推开了门。她初来乍到,发现属于她的雨水已然有限。她可不着急,她拥有四月雨水的足够份额。
秩序
繁花虽繁,却不会乱来。它们恪守律令,性子再急,也不会僭越物候与节气。人们所偏执的文艺描述,在自然的秩序里是不可想象的。 一切都得按照秩序册来。梅花推门见雨水,桃花推门见春分,梨花推门见清明。虽然在时序的衔接中,繁花时有互见,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为了什么目的而起了争执。“俏也争春”,或者“俏也不争春”,统统都是误解。无意的,或者有意的。 即便众多被人们使滥了的主观之词本无恶意,也跟诽谤讥诮差不离多少了——繁花虽繁,却何曾这般争来争去? 在自然的秩序里,繁花各司其职,各有其命,各安其分。但文艺的伦理却是,宁作只见其乱的线条和色块涂鸦,宁陷“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意错觉,也无意于尊崇其本然的秩序。 人类有故意滥用这种文艺伦理的嫌疑。但是把自古以来人类所有的滥用叠加起来,也无法抵消这样一个事实: 一切光的明灭,一切色的冷暖,一切形的荣枯,俱在自然的秩序之中更替。看尽繁花,眼迷心迷之余,还需认领这一份秩序。
安放
花开花落你都在场,也算善始善终。 失去水分的梅瓣落满肩头而不去掸拂,因为每一瓣被你接在生命里的落梅都值得善待。请你平心静气,坐在一棵梅树下,目送一万棵梅树落雪。这场浩瀚花事的无声退隐,将教育你,让你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热爱美。 你向一场花事的盛衰里寻觅,更多是安放。确切地说,是寻求安放。在你被草率安放之前,你始终没有停止为自己寻觅一个安妥之所——你等不及身后事,一旦把事情拖到身后,你就彻底丧失了主动权。 你当然知道结局就是如此。“生命终究是一个悲剧”的额外意义就是,在大概率上,你是得不到自己所满意的安放的。但是倘若现在就找到安放之所,情况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必须指出上述表述中的概念偷换——或者重叠——灵魂的安放似乎完全可以先于骨殖而搞定。这太难了,但理论上行得通:它不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所在,也非纯粹的时间。 一个精神坟茔。在花开时,也在花落处。在雨水,也在春分。是一万棵梅树开放有序的时空,也是一瓣落梅从肩头坠向池水的时空——它终归是个精神性的所在,而附丽于物质性的美。 善始善终地善待自己,就是把自己安放在花开花落的所有所在。用精神的喜剧抵抗生命的悲剧,意义本不在输赢,而在其本身的壮怀激烈和喜悦吧。
奖赏
在春天的郊野公园健步而行,我将获得什么? 雨水。是的,我将获得雨水的奖赏。这不是一次交换,是奖赏。所有在春天里甩开膀子行走的都将获得奖赏——雨水给我的,不会多过给一棵尚未返青的水杉的。它在灰色的天幕下裸露着,看似还没完全缓过劲儿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一条小溪正在它内部行走。我能确认一棵水杉在春天的行走早已出发,早于我,晚于一棵扦插不久的柳枝。 花香。是啊,我将获得花香的奖赏——花香并不热烈——事实上在雨水中它淡到极致,而这正是我所获得的奖赏。是一园子盛开的梅,把骨头里的香气悉数倾倒给春天,和在春天里行走的人们。这仍然不是一次交换,而是一份来自大自然的慈善照拂。我能做的,唯有领受和被唤醒——或许我仍然是贫瘠的,我既是土壤,也是种子。 来自春天的奖赏远不止雨水和花香。 我听到了一声声悠长的鸟鸣,和蚯蚓拱动花地的声音。那被腐烂的旧秸秆覆盖的花地里,秋英草的雏秧正攒着劲儿准备拔节。一切,组成一个季节的伟大心跳。一切,都是奖赏。 我们在春天里行走,就是为了获得与之谐振的心跳和力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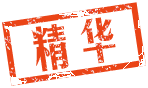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