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iahan 于 2020-3-7 01:46 编辑
诗的见证在米沃什那里尽管有着特殊的涵义,但已经在诸多诗人的写作中拥有了普遍的认同并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那便是诗人对于经验的有力回应,而最终转化为“唯一的现实是那艺术作品本身。……在诗歌中这现实恰恰正是词语”(语出曼德尔施塔姆《阿克梅派之晨》杨青 译)。在当前这场疫病灾难中,我们的诗人们亲历其中并施与极大的共情,以不同的方式写出了既符合人之常情又以“新的感觉为基础的”(塞萨尔·巴列霍)诗的文本。 自然,身在重灾区的诗人能够把身边的生活体验转化为诗,无疑会构成一个在场者有力的见证,或者说,这是一种直接拥有的诗的伟大力量。杨汉年《在禁足的日子里》如此开门见山地写到:
口罩之外都是呼吸的禁区
这是颇有意味的一个诗句,不妨说,诗人在这句诗里蕴涵着更多想说而不能说或不宜说的痛楚。所以,接下来,诗人只提供几个生活的细节:"室内,一个公职人员/正在拖洗地板/整天守着延长的假期""洗漱后,我站在窗前/看朝霞落入空寂的大街“”戴着袖章的人让我签字/外出事由的一栏/我填写的是:寻找空气“,写得质朴、沉实而不事雕琢,但就在这份貌似平静的白描里,蕴含着诗人复杂的心思,乃至于你可以在这里发现聂鲁达般的“你可知道死亡来自何处”的深沉忧郁和令人不知所措的无边的惊悚。 同样,我们在黍不语《隔离》这首诗里体会到其身处灾难之中所拥有的某种无着与无奈:“窗外只有无辜的白云/和无辜的蓝”“我在久居的房子里蜷缩,说不清是隔离/还是躲避”,在“太多的声音/聚集/又消失”的恐怖中体验自我的失去与游离:“我没有听见自己的声音/仿佛我已没有声音”——这里拥有着一份真诚的心思,惟有此,才使“仿佛我只能在这样别无选择的虚空中/去等待一些事物的重建”在那一刻显得合乎情理,而“每一个/在迷雾与寒冷中等待醒来的人”(《那边》)“一个人在死去,被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死去,不被我们看到”(《叙事》)才给我们带来意外的震撼。 作为湖北籍诗人,即便客居异国他乡,灾难也依然会牵动其心绪,看到王家新的《给——》就知道,他在为同乡的苦难作一次远距离的举证,
巴黎,卢森堡公园附近的街区 听到你“最终”离去的消息 我的妻子哭了 在巴黎的夜空下哭了
此刻,诗人说:“我没有哭。但是我睡不着”,他在反复地看着那张训诫书,“直到黎明前的最后一阵黑暗袭来”,直至看到亡者“大睁的眼睛即使在黑暗中/也在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何等悲切的图像镌刻于诗人内心深处!无疑,这是一个诗人对于故乡无辜的罹难者最深切的哀悼。这里印证着一位学者(罗新)的谈论:我们对失去的生命,对仍然处在痛苦之中的、前途未卜的人们感到伤痛,但大家说的“愤怒”主要不是来自病毒的直接打击…… 艾略特在《哲人歌德》这篇文章里写到:“智慧是直觉的天赋,经验使它成熟,使它能够理解事物——活生生的事物,尤其是人类的心灵。”(樊心民 译)我们看到,在对于灾难的观察与反思中,总会有人进入诗的知性展示从而拥有语言的洞见。海因的《庚子避祸录》在同类的写作中就有对于事物本质的揭示,比如在疫病蔓延的日子里,各种各样的死亡随时发生在某个街道、小区或家庭,那么:“在/就是当下最好的消息”(《消 息》)才有让我们觉得一言中的的真切;《游戏》里,在“又是一家人蜷缩一起的日子”“是退缩到命门时的/绝地反攻”的述说里,勾勒出自我隔离的图景,而这一切都在“刺猬就经常扮演这样的苦主”里发生语义的逆转;在《棋局》里,一局棋因了众所周知的缘由,
……误入死局 如今是面对着天下人 又不能随意悔棋 所以至今不尴不尬 没有结局
联想到个人,则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是谋局者/又是那一开始就被操控的/着了魔的挣扎小卒/出乎于尔,反乎于尔/置身这无望的/生活里/谁还会在乎/一局棋的/无趣",这无疑是一副绝妙的荒诞世相图,不无讽刺,又弥漫于无奈之中;而一旦陷入“要么不知所踪/要么行将倒毙”(《发现》)的人生际遇,那并不是诗人观看的末世来临的欧美大片,而是其当下某一刻身临其境的“发现”——诗人就是在如此悖意的体验中,挖掘出一种独属于自己的新的感受力。 面对灾难带来的纷乱世相,作为一个诗人,有时候也会陷入迷茫的无所适从的状态,而在接下来的多日的观察与思索中,会进入审美的艺术幻觉,而于直接的生活断面的截取和直抒胸臆的路径之外,或许还有另外的蹊径,那就是变形的暗示和隐喻之下的词语的异类,这样的曲隐依然可以实现其“远离其原初的存在,历经一种特殊的、扭曲但不失其真的想象”(罗兰·巴特)。在蒋立波《当你谈论灾难与诗》里,就有如此绝妙的情境:
宿主开始互相甩锅,吵醒蝙蝠倒悬于客厅的美梦。 死神与病毒表演的双簧不会穿帮
诗里的“甩锅”“倒悬”“双簧”的出场,还有“仓库里/囤积的口号终于告急”“更多的死者/排队进入焚尸炉"让诗呈现出迷幻而荒诞的色彩,同样有一种表象悖异下的深刻揭示,给”写作的羞耻无法被谈论“一个坚实的注脚,在这种多元化修辞的背后,诗人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诗意裹挟与审美的深刻以及诗的样态的驳杂与复合性,同时,也让一首诗在灾难背景下折射出现实深层的复杂而诡异的本相,并拥有了诗性意义上的完整性。 布莱希特的《我总在想》如此写到:“最简单的话/已足够。当我说出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的心一定会被撕成碎片”(黄灿然 译)。诗人道出一个写作真相,那就是说出事情是什么样子,在当前的灾难中,你质朴的记述往往就是一个难得的见证,可以写出诗篇,也可以像诗人小引那样以日记的形式如实的描述。也可以效仿普里莫·莱维的理智,他在希特勒当年始于暴行的时候,作为一个幸存者,“从未选择愤怒控诉,避免情绪化宣泄引发逆反,而是选择以最理性冷静的方式叙述所见所闻”(见叶克飞《奥斯维辛没有幸存者,最好的人最早死去》)。我们看到一位95后女孩如此的表达:“在太阳都喊热的地方,传播死”(桉予)所拥有的内在的力量,这里尽管有着某种悲观的情绪,但却依然有着作为“记录者”的谦卑的诚实。与之不同的是,“当药水被眼水审判”,“整个天空是最轻薄的肺部”,道辉在如此天问般的诗句里,让死亡的悲情降临人世间,无疑在给这场灾疫提供着一个变体的词语旁证。无独有偶,阳子也从“洗涤的水泼向天空”而思忖着如何摆脱一摊污迹的围困,最终落脚到平民之死和英雄之死的苦难现实之中,可以说,这是远离灾难中心而又在灾难之中的人对于灾难本体的辨认与沉思,我们但愿如此犀利的诗句原本不该发生而就这样居然发生了——这本身就构成灾难本事的共体,所幸的是诗人最终意外地完成了对于现实救赎意义上的文本真实和实在,从而构成“一种抵抗死亡的坚定的论证”(阿米亥)。 2020.2.23 兰石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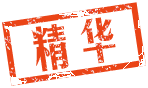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