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诗的形式问题,一直是困扰诗歌理论家们的一个心结,然而,百年新诗迄今,不要说“诗体重建”“诗体规范”等等的追求,已显得愈来愈渺茫,就连新诗应具有什么基本形式,除了分行这一点似乎已达成某种共识外,其余的仍是莫衷一是。然而,倘若因此说,新诗根本就无须具备什么形式,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任意挥洒,恐怕又要受到诗人与理论家们的一致反对。因为你无法举证出一首曾受到广泛赞誉的新诗,就一点形式也不具备,即使是一首劣诗,你也可以从中辩解出某种形式的存在。因此,新诗的形式问题,不仅还要继续探索,其探索的空间,实际上比古体诗(本文所言古体诗主要是指古典格律诗)还要阔大。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来着重探索一下新诗的形式感的问题,之所以要在“形式”后加一个“感”,是因为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形式更适于严整的古体诗的研究,形式感更适于自由的新诗的探索。当然,为了行文的方便,它们在这篇文章中常常会交混使用。 诗歌的形式,在文本中,是由诗歌的外部形态,及诗歌的语感节奏,意象的表现,诗思的运动所构成的,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而诗歌的形式感,则是读者在对诗歌文本的阅读中,对构成诗歌形式诸要素的一种感知,模拟反应,它不可避免地在形式的客体上,打上了主观的印记。因此,一位论者在谈论一首诗的形式构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谈论自己对这首诗的形式感。 对新诗的形式规范一直持激烈的反对态度的叶橹先生,早已敏锐地意识到了新诗的形式感的意义,他在他的《自由,格律和形式感》一文中指出:“有形式感,是一首成功的诗作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或许,我们可以把叶橹先生的话再稍加发挥一下,就是任何一首真正的新诗,都必须具备一种鲜明的形式感,并以这形式感的鲜明程度,来作为判断一首新诗的优劣高下的重要依据。之所以将新诗的形式感要求到鲜明的程度,是因为我们在散文文体的阅读中,同样可感到某种形式感,但它们无须达到鲜明的要求。 谈论新诗的形式感,显然离不开古体诗的背景,古典诗在外在形式的完备完美上,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一套严密的平仄、对仗、音韵的体系,是新诗所无法做到的。然而,另一方面,这无法逾越的形式高峰,也是新诗另辟蹊径,发展新的形式的动力。可以说,诗歌的形式的天地,是广阔的,无限的,古典诗只是占据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百年新诗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有展望的理由或资格这样说,在形式或形式感上,现代新诗的摇曳多姿,与古典格律的典雅庄重,各有其价值所在。 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一文中,论及古体诗与新体诗的不同时,概括为三点:一是“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律,但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二是“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创造的。”三是“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一段话具有着深刻的诗学洞见,这里,我且套用闻一多先生的语式,并将概念扩大到“形式”,就是:一,古体诗的格律形式是有限的,但新诗的形式是层出不穷的;二,古体诗的格律形式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形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创造的;三,古体诗的格律形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形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我的套用对于复杂的古体诗的世界,或许过于简单了一些,但于新诗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基本是适用的。 无论是古体诗,还是新诗,在形式上还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外在形式是诗歌作品外部的直接表现形式,是诗歌内容的感性呈现,一般而言与内容不直接相关;内在形式是诗歌内容诸要素的内部联系和构造方式,它与诗歌的内容血肉相连,属于深层次的形式因素。古体诗与新诗的实践都表明,外在的形式是有限的,而内在的形式是无限的;外在的形式是古体诗的擅扬,而内在形式正是有待新诗开拓的无限疆域。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所要着重探讨的,主要是新诗的内部形式,尝试由几首新诗中的名篇,来探讨新诗的节奏、意象的表现、诗思的运动所呈现出的几种形式感。
(二) 讨论新诗的形式与形式感,闻一多的理论与实践,无疑是一个重镇,他的“三美”理论,影响了一个时代,他创作于一九二五年四月的代表作《死水》,是新诗史上不可忽视的名篇。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
《死水》一诗,极好地实践了闻一多自己的“三美”理论,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死水》给予读者的形式感是极为鲜明的。尤其是,在外部形式上,全诗5节20行,每节4行,每行9字,令人联想到古体诗的整饬美。在语言结构上,每行都是4个音尺,每个音尺都是由2个或3个字构成,给新诗带来了一种独特的节奏感。 《死水》的颇具古典建筑特色的形式感,是新诗史上的一个醒目的存在,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它虽有为数甚多的仿写者,却鲜见有成功者,而最终成了一个孤本。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如果分析一下,《死水》在外形上的“豆腐干”形,“戴着镣铐跳舞”的节奏,刚好与诗作的主题,即所要谴责的“死水”世界的封闭,僵化,形成的某种契合,显然是这首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换一个表现的对象,如微风,或流水,这种“豆腐干”的外形,戴着镣铐的节奏,恐怕就不会取得《死水》中的效果了。因此,闻一多的“三美”理论,虽在理论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他的创作实践。百年新诗的实践已证明,每一首诗的形式,都应与这首诗的主题,及作者的个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方能获得读者的认可。而作品的主题与题材是取之不竭的,每一个诗人又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生命个性,它们的组合,决定新诗的形式必然是无限繁多,不可重复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每一首成功的新诗都应有着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形式感,它们可以相互影响,但不应追求古体诗那样的形式规范。 《死水》的形式探索,在新诗史上,有其独树一帜的价值所在,但若放在整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仍是存有缺憾的,有误入歧途之嫌。其一,闻一多的初衷,是想以《死水》的形式探索,为新诗树立起一个榜样,但结果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并非新诗的康庄大道,这就局限了《死水》在形式上的价值;其二,《死水》整体的9字一行,以及每行的4个音尺,每个音尺由2到3个字构成,总令人联想着古体诗的平仄格律,但与古体诗在这方面所达到的完善完美的程度相比,它们又显得大为逊色,反而不利于对新诗价值的判断。其三,对于《死水》这样堪称杰出的诗篇,我们理应有更高的形式感的要求——诗思的运动之美。或许是闻一多过于关注“三美”的布局,《死水》的场景虽不断有拓展,诗思却始终在一个层面上推进。诗尾的“不如让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虽情感饱满,但终是激愤之语,不能在诗思的运动上更进一层。一首在深刻的象征上,有可能成就伟大的诗篇,终于只能在半空盘旋,成为新诗的遗憾。
(三) 新诗的形式探索,由初创期发展至闻一多,迎来一个转折,由闻一多发展至戴望舒,又迎来一个转折。戴望舒是在闻一多的基础上前进的,他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仍有着借鉴的意义。 戴望舒的早期创作,受新月诗派和中国古典诗词的双重影响,在形式上有着显著的“三美”特征,追求严整的格律,音节匀称,声调抑扬,韵律和谐。但在翻译西方诗歌的过程中,有了更大诗歌抱负的戴望舒,很快敏锐地意识到了早期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并且一再地指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诗论零札》 戴望舒的理论和实践,将新诗从当时新月格律的纠缠中解放出来,呈现出一个新的广阔的天地。成熟期的戴望舒,将口语化的语言用散文化句式连缀起来,以自然的口语的节奏,取代过去诗行中追求的所谓格律,以诗情的抑扬顿挫的起伏,来推动诗篇的运行。今天的新诗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在戴望舒的理论和实践所开拓的大框架里行进,只是在技术上显得更圆熟,更丰富了。 发表于2008年《诗探索》第二辑上的庄晓明的诗论《纯诗——一种脉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戴望舒诗歌理论的一种承继。文中指出,诗的脉动可以有以下几种形成方式: - 1. 韵律、节奏形成的脉动。
- 2. 文字、语言形成的脉动。
- 3. 情感、情绪形成的脉动。
- 4. 诗思、思想形成的脉动。
这其中的第3种和第4种脉动,主要呼应的就是戴望舒的“诗情的抑扬顿挫”。在物理学上,诗的脉动,或“诗情的抑扬顿挫”,会形成一种波形线,这种波形线实际上就是诗的形式感的一种表现方式。在戴望舒的创作中,《我用残损的手掌》是这种“诗情的抑扬顿挫”运用得比较成功的杰出诗篇之一,我且尝试着用诗的脉动说,将这首诗的形式分析一下。写作这首诗时,诗人在香港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拷打,关在黑牢里,然而,他的诗情比任何时候都更浓郁地喷涌而出: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 那里,永恒的中国! ——《我用残损的手掌》
开篇的两句:“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是诗篇进入超现实诗境的引子,用的是一种平静叙述的语气,表明此时的诗情是在水平轴上。随后的第3句中的“灰烬”,第4句中的“血和泥”,则呈现了古老土地的浩劫,沦陷,以及热爱着这片土地的诗人的痛苦,因而诗情是一段向下的波形线,在水平轴之下 ;为了逃避国土沦陷的痛苦,诗人转入了对曾经的家乡的回忆:“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春天与家乡的无比美好的回忆,于沉陷痛苦的诗人,显然是一个拯救,并使诗情的波形线凸起在水平轴之上 ;但春天与家乡的回忆,终究很快过去,诗人的触手,无可避免地又触入现实的冰凉。由“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到“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这一大段,诗人哀故国沦陷的诗情,由一个个寒冷、萧瑟的意象呈现,从而使诗情的波形线大幅地下落到水平轴之下 。由“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至诗尾的“那里,永恒的中国”一段,诗人的探寻的触手终于摸到了希望所在,对“辽远的一角”的信任,期待,以及与“爱”“希望”“太阳”“春”“苏生”等温暖明亮的词语的合力,终于又将诗情的波形线拉到了水平轴之上 。 当然,我为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所描出的波形线,只是其中的大跨幅的脉动。在每一段波形线的内部,我们还可以寻到小的脉动,它们的存在,有效地增强着大的脉动的幅度。可以这么说,《我用残损的手掌》这首诗的绝大的艺术感染力,来自于它的诗情的抑扬顿挫,或脉动,它的鲜明的形式感的成功,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仍有着借鉴的意义。
(四) 新诗发展到北岛,在关于形式的理论建设上,似没有出现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但在形式的实践上,却达到了新的高度,形式感显得更为鲜明,纯粹。不仅戴望舒所倡导的“诗情的抑扬顿挫”有了更完美的呈现,诗思的运动——这更为难得的形式感,亦抵达了新的境地。北岛的诗篇《回声》,可谓这方面的一首杰作。
你走不出这峡谷
在送葬的行列
你不能单独放开棺材
与死亡媾和,让那秋天
继续留在家中
留在炉旁的洋铁罐里
结出不孕的蓓蕾
雪崩开始了——
回声找到你和人们之间
心理上的联系:幸存
下去,幸存到明天
而连接明天的
一线光线,来自
隐藏在你胸中的钻石
罪恶的钻石
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
被送葬的是你 ——《回声》
峡谷,无疑是《回声》诗的中心意象。在地理上,峡谷乃指由峭壁所围住的山谷,一般由河流长时间侵蚀而成。因此,在诗意上,峡谷可看成是一种风与水的通道,虽然曲折艰难。但在北岛诗的首句,“峡谷”突然“走不出了”,成了一种迷宫,这就形成了诗的第一个顿挫;第2行中的“送葬”,第3行中的“棺材”,意味着死亡的封闭,消失,而第4行中的“与死亡媾和”,又意味着生与死的界线的消解,这就形成了诗的第二个顿挫;第4行的“秋天”,本意味着一种广阔的收获,但随后第5行的“家中”,第6行的“洋铁罐”,则对这秋天的广阔作了令人窒息的压缩。第7行的“不孕的蓓蕾”,更对“秋天”的收获进行了彻底的颠覆,这就形成了诗的第三个顿挫;第8行的“雪崩开始了”,有着“崩溃”“革命”等等的寓意,它本应引来一个新的世界,但第9行的“回声”,则又令人联想到“重复”“折腾”等历史的梦魇。第10行第11行的“幸存/ 下去,幸存到明天”,更是对前面“雪崩”的宏大历史性场景的回避,否定,至此,诗篇一波三折地形成了它的第四个顿挫。第12行第13行的“明天”“一线光线”,令人联想到早晨,新生,新的开始,第14行的胸中的“钻石”,令人联想到某种美的结晶,一种“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升华,但15行的“罪恶的钻石”,随即对之作了反讽的否定,似乎这个世界本就建立在一个“罪恶”的基础之上,由此形成了诗的第五个顿挫;第16行的“你走不出这峡谷”,是对诗的开篇的回应,但这里,“你”至少还在走着,折腾着,随后的17行,也就是最后一行的“被送葬的是你”,突然来了一个深化的转折:你走着,却已经死去,被送葬。这是一种何等的个人或时代的悲剧,诗篇至此完成了它的最后一个顿挫。 《回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一个成功,是它在意象的不断转换中,还呈现出一种诗思的运动之美,这是一种更为内在,更为深层的形式感。北岛的诗思的运动,往往通过隐喻、通感、联想等来提供动力,《回声》的运动是这样进行的:由走不出的“峡谷”的联想,引向一种“送葬”的“棺材”;由“棺材”寓意的死亡,引往凋零的“秋天”。又由“秋天”固有的归宿的意味,指向“家中”;由“家”所包含的日常生活,指向“炉旁”,及炉旁的“洋铁罐”。再由“洋铁罐”所隐喻的一种封闭,及与本土的疏离,指向“不孕的蓓蕾”;“不孕的蓓蕾”寓意着一种存在的极限,无望之后,必然地,革命性的“雪崩开始了”。“雪崩”的“回声”的威胁,自然地引起了峡谷里的生存者的惊惶,而寻求着如何“生存下去”;“生存”,意味着还能见到“明天”,及明天的“一线光线”。这“一线光线”的珍贵,不由令人联想到“钻石”的折射;但宿命的是,这“胸中的钻石”,又与人类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罪恶”纠缠在一起。正因为这种本质上的“罪恶”,决定了“你”的生存是无意义的,“你”所在的“峡谷”,就是“送葬”的棺材。诗思的运动至“被送葬的是你”嘎然而止,但其运动的惯性,仍在读者的思索中延伸。 《回声》的意象的呈现,亦颇有特色,随着诗思的运动,诗的上半部分由巨大的意象“峡谷”,逐渐转换至微小的意象“蓓蕾”,诗的下半部分由巨大的意象“雪崩”,逐渐转换至微小的意象“钻石”,这些都给了读者一种清晰的形式感。 北岛另有一首诗《触电》,其层层递进式的诗思运动,在新诗中更具有着普遍性,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一读,以欣赏其形式的魅力。
(五) 诗歌的外在形式,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是古体诗的长处,新诗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其实,由于新诗的自由的基因,其外在形式的发展潜力,尤其在文字的排列方式上,同样有着丰富的发展空间,且与内容的关系,也要比古体诗更为贴近一些。新诗的不同时期,都有诗人在这方面作出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努力,并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形式感。 我们先看一首戴望舒的短诗《白蝴蝶》:
给什么智慧给我, 小小的白蝴蝶 翻开了空白之页, 合上了空白之页?
翻开的书页: 寂寞; 合上的书页: 寂寞。 ——《白蝴蝶》
诗中第一节中第3行第4行重复且对称着出现的“空白之页”,与第二节中第1行第3行重复且对称出现的书页,以及第2行第4行整行的“寂寞”的重复对称,令人联想到蝴蝶的那一对翮动着的翅翼,而造成一种鲜明的视觉感受。这些词语在诗篇中的轻盈如蝶翼的闪现,不仅给读者有蝶舞花园的感受,而且使诗篇的诗思更为灵动,意境更为隽永。 台湾诗人林亨泰有一组诗《风景》,对新诗外在形式的探索,也有着自己的贡献。我们且看其中的第一首:
农作物 的 旁边 还有 农作物 的 旁边 还有 农作物 的 旁边 还有
阳光阳光晒长了耳朵 阳光阳光晒长了脖子 ——《风景》(一)
诗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矩形排列,令人联想到整齐的田畴,并使得诗的中心意象“农作物”一出现,就似乎绿油油地摇曳起来。第一节诗中,反复出现的“农作物”等词,不仅给了读者以田间植物行行排列的视觉形象,而且第3行和第5行的“农作物”,既是前一句的宾语,又是后一句的主语,排列构思之巧妙,令人叹服。《风景》一诗在形式感上的成功,既令人联想到古体诗,又真正地逾出了古体诗。 古体诗中的隐题诗,颇受读者喜爱,有不少流传至今的佳构。而当代大诗人洛夫亦在新诗中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其创作的数量之多,题材之丰富,内容之深刻,都可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试看他的隐题诗《蚯蚓一节节丈量大地的悲情》:
蚯 蚓饱食泥土的忧郁 一腔冷血何时才能沸腾? 节节青筋暴露 节节逼向一个蜿蜒的黑梦,一寸一 丈地穿透坚如岩石的时间 量过了大草原,再量 大峡谷,天翻 地覆之后它仰起黯然 的头 悲怆,淡淡的 情感,土土的 ——《蚯蚓一节节丈量大地的悲情》
这首诗灵活地运用新诗的跨行句法,使巧妙地安置于每一行的首字竖着念,刚好就是这首诗的诗题,从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形式之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首诗没有为形式而形式,排除了古体诗中常见的游戏性,通过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对诗题的强调,帮助诗篇深刻地挖掘出一种存在的艰辛,困苦,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总之,新诗的形式及形式感,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因着其自由的基因,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索,创造,丰富。它是一个没有边际的花园,它的独特的风貌,它的脉动之美,诗思之美,终有一天会把更多的读者引入这座摇曳着无数诗人生命的花园,忘返而留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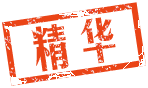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