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西厍本人 于 2021-2-24 10:01 编辑
读费尔南多·佩索阿诗歌《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
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
诗/费尔南多-佩索阿
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 你只是虚度了它。无论你怎么活 只要不快乐,你就没有生活过。
夕阳倒映在水塘,假如足以令你愉悦 那么爱情,美酒,或者欢笑 便也无足轻重。
幸福的人,是他从微小的事物中 汲取到快乐,每一天都不拒绝 自然的馈赠!
诗以议论入题。首节用一个不容置疑的判断,说出诗人对于生活的灼见(也许是偏见):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虚度了它。这并非诗人视“不快乐”如不见,而是面对“不快乐”给出了自己的逻辑确认和价值判断:“不快乐”,即“虚度”,即意义的虚无。“只要不快乐,你就没有生活过”,这个条件句亮出了诗人的生活观、价值观甚至世界观:唯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生活才是真实的,人才算真正的“生活过”。 第二节以一个自然的场景,对首节的抽象议论进行形象诠释——或许从表达技艺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补救?“夕阳倒映在水塘”,一个再庸常不过的自然景致(自然细节),其中“真意”并非人人辨得悟得,一旦辨得悟得(令你愉悦)——像梭罗和陶渊明那样,则世俗生活中的某些事物——爱情、美酒、欢笑,或者其他任何事物,也将显得“无足轻重”。诗人的价值取向于此昭然。 第三节则又回到抽象的议论中,以判断句的形式给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幸福从来就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快乐体验,而这种体验时时考验着人们对于自然馈赠的态度——每一天都不拒绝——诚实而虔诚地接受自然的馈赠,幸福之泉将永不枯竭。诗人对于自己的感悟多少有些偏执,因而不惜以议论出之,直接,明晰,不绕弯,不装神弄鬼。 所以这首诗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议论在诗歌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议论本身的精警,取决于它对生活真谛的洞察和烛照。在很多人看来,议论入诗是有风险的,因为议论的主观性难免伤害诗意的呈现——诗意的呈现,在很多人那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而排斥议论,自然成为了这种共识的一部分。但是在佩索阿的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议论的意义,虽然它仍然需要借力于一个“客观”的自然细节。或许在真正的诗人那里,某些清规戒律是毫无意义的。
2021.2
读风荷诗歌《有感于膝伤》
有感于膝伤
诗/风荷
读到里尔克的那首《豹子》
猛然想到
我的膝盖骨里围困着一头牛
一头老态龙钟的老水牛。它低头在河边
慢吞吞地喝水,啃草
它体积庞大,一点也不轻盈
“要是我的身体里,住着一匹骏马就好了”
它挺拔,它会跑得又快又欢
而现在的情状是一头牛代替着我
一脚一脚踱步
缓慢地拉犁、耕地……
但并无悲伤啊。你看这头牛
它瞳仁明亮而清澈,没有昨夜风雨留下的咽呜
它慈祥,安静。和时间握手言和
诗人风荷对于生活所赐的痛苦有着极其敏感的感受力和诗意的转化力。
“膝伤”带来的生理性痛苦好多人都经历过,但未必人人都能将它转化为一种心理体验予以深刻的审美观照,风荷却独出机杼,把“膝伤”想象成“膝盖骨里围困着一头牛/一头老态龙钟的老水牛”,“它低头在河边/慢吞吞地喝水,啃草”——这种对于身体伤痛的化虚为实足见诗人对苦难的审美处理和消解能力。
对于“膝伤”给人身心造成的持久摧折,诗人一反常理,在医疗手段未及奏效的间隙,沉溺于假想,“要是我的身体里,住着一匹骏马就好了/它挺拔,它会跑得又快又欢”。她把对健康的渴望寄托于“一匹骏马”的想象——与其说这是对生理痊愈的诉求,毋宁说这是对精神超越的渴求。诗人的生命感在“骏马”这个意象中得到了鲜明的昭示。而现实的苦厄境遇则是,“一头牛代替着我/一脚一脚踱步/缓慢地拉犁,耕地”。对身体苦痛的细腻玩味和形象化“转移”,大概是诗人才具备的“超自然”能力。
那么,诗人是否真的就此限于苦厄的玩味而无法自拔了呢?不,事实上诗人以强大的精神转化力实现了自我救赎和超越。她说“并无悲伤啊。你看这头牛/它瞳仁明亮而清澈,没有昨夜风雨留下的咽呜/它慈祥,安静。和时间握手言和”。诗人的精神之瞳“明亮而清澈”,才能“拂去”生活的“风雨留下的咽呜”,进入到一种生命的“慈祥,安静”境界。“和时间握手言和”,固然算是一种妥协之术,其实更是一种精神澄明和灵魂通透之境。
至于诗人在诗的开头说,这首诗是在“读到里尔克的那首《豹子》/猛然想到”自己的膝盖骨里“围困着一头牛”,实在是一种诚实的没有城府的交代,表明自己的诗性感发自有来处。诗人当然也可以“聪明”地直入正题,似乎更显直截和简洁,同时诗意也更显集中和专注。但是诗人自有考量,或许她想要的,正是在一首诗的内部达成诗意的互证和审美空间的拓展。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在不同的文化那里,诗人对于生存困境的审美取向和趣味是那么不同,又是那么气息相通,互文见义。诗人这样写,等于承认自己的诗写是承续了里尔克(们)的传统的——尽管她骨子里的这头“牛”比“豹子”更具东方意蕴。
读张敏华诗歌《“悲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悲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诗/张敏华
想父亲了。父亲在厨房下面条, 满屋的水蒸气,他忘了 开油烟机。透过厨房的玻璃门,我只能 看到父亲穿着灰色内衣 晃动的背影。
想念父亲了。父亲就在那里—— 停电,蜡烛被点亮, 虚掩的卧室门 被推开:还是那张床,那盏灯,那把藤椅,那本相册, 那些说话的声音和神情, 但我再也看不到父亲瘦弱的身影。 “宿命,终究是虚无。”
窗外是秋天,银杏叶开始变黄, 但我不会将地上的银杏树叶 叫枯叶。 不可说,不能说啊—— “悲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诗人张敏华写过不少亲情诗,尤其在他父亲过世之后,他的那些关于父亲的诗更显切肤之痛,隐忍而深刻,颇能引人共鸣。这首《“悲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其中之一。 诗开篇就直陈“想父亲了”,所有迂回婉曲都显得多余,都被诗人舍弃。在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里,处处有父亲的气息,父亲的灰色身影。“满屋的水蒸气”里氤氲的,是在老境里混沌的父亲的日常——“父亲在厨房下面条”,是诗人信笔所及的父亲的日常印象,是父亲留给诗人的充满温度和“湿度”的记忆的切片,可能有些模糊,却如水印般洇渍在记忆的册页,难以被时间之水洗除。 诗的第二节说“想念父亲了”,一字之差平添了一份深沉和庄重。父亲离开了,他还在那里,就在那里——卧室虚掩,作为生命存在的父亲早已羽化和散逸,但是他的气息,他的灵魂无处不在。床是父亲,灯也是;藤椅是父亲,相册也是。父亲似有万千法身,附着于每一件日常之物。 厨房和卧室,父亲生前盘桓其间的两个生命场域,构成这首诗看似逼仄实则幽深的审美空间,使得诗人的记录有了“信史”的性质和真正意义上的“事实的诗意”。 生命的殒失是一种必然。在哲学的高度,诗人确认了“虚无”乃是一种宿命,无法逃避。但是这种看似理性的认知并没有替换掉诗人失怙的感情伤痛。只是,诗人把这种伤痛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断地涵咏品咂,转化成了一种审美行为。或许,只有在这种审美转化中,诗人的失怙之痛才会略略减轻一点。 但是,诗人仍然显得敏感和小心翼翼,不敢轻易触碰“死亡”这个词,甚至不敢触碰“死亡”的替代词——诸如“枯叶”——不可说,不能说,仿佛不说就可以减轻甚至免除痛楚和悲伤。诗人似乎寄希望于时间来冲淡一切,但他仍然清醒地知道,“悲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唯一不确定的,是悲伤是否有一个尽头,一个终结。或许正如史铁生所说,悲伤也成享受。如此,诗始于“想念”而终于“思”,有了一个审美的升华,因而免于庸常的抒情。
202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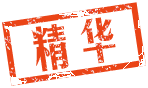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