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侍仙金童 于 2024-2-1 10:22 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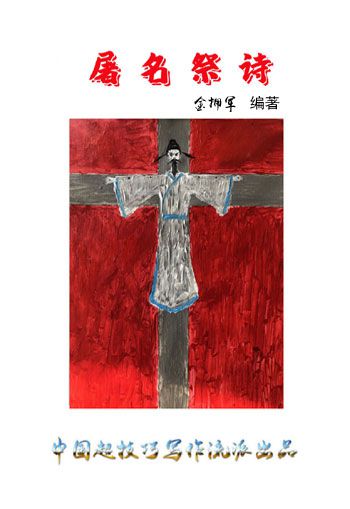
1 流星划过的时候 我的身体,在瞬间 被光明烛照,我的皮毛 燃烧如白雪的火焰 (主角出场之前的渲染,是雪豹也是动物学家乔治夏勒,首先这个出场环节的设置是中规中矩的,就像中国功夫各门派都有的起式动作,所以这一段可以挂个美名:白鹤亮翅。不过按照参赛的徐志摩微诗赛的徐志摩标准,显然这个起势,并没有什么出奇的诗性。被拔高的作品必须用高标准来研判,这个反方应该没有异议吧?这个开篇与徐志摩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有没有可比性?我觉得可以意会地去比,而不需要用文字表述出来,这才是更高级的心理层面的亮分。徐志摩诗歌奖,好歹也要沾点徐志摩的文风,否则挂羊头卖狗肉也是符合工商管理法的,既然为了抬举吉狄马加的诗偏要塞奖给他,不如就叫吉狄马加诗歌奖算了,就像这几天A股主力拉升中石油、银行这类自家股一样,何必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搞。但是这句败笔在于,既然是能看出雪豹身体被光明烛照,肯定是在夜里,那么雪豹的皮毛的颜色怎么会是白色?再说,白雪一般的火焰,对于渲染雪豹这种独行侠的形象,没有一点辅助作用,这一笔做得基本是无用功。好的诗,尤其是写雪豹这个孤傲威猛的狠角色,开篇适合刚性的文字,“咣”地一下把读者的视线抓过来,或者徐志摩式的“柔”字切入,逐步展开雪豹的威猛也可以,总之比光的烛照的构思要强百倍。 这里我选自己的作品,既有徐志摩“轻轻的”痕迹,也有吉狄马加这段的”烛照“,打败长诗不一定要用长诗:《英雄曹军:轻轻的我走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泪流的妻儿\那火红的党旗\温暖着卫士的胸膛\烛光里的身躯\保持着永恒的刚强\那落水的孩子\又能在阳光下奔跑\对党忠诚的战士\还会纵身扑向波涛\在这名为凤凰的村庄\你会看见涅磐的红光\我将重生于梧桐树上\继续放飞护林的梦想\佩戴好警徽肩章\向革命先烈靠拢\共产主义信仰\就在平凡的言行中\为人民牺牲光荣\奋不顾身越战越勇\烟雨蒙蒙难舍难分\难分难舍烟雨蒙蒙\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手\永别了亲人\永别了战友\2009.8.22) 我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 犹如一条银色的鱼 消失在黑暗的苍穹 (“我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表述也不准确,因为“暗影不可能是有光”应该是“我的身影”相对准确,因为身影指身体运行速度快形成的视觉拖影,影子指身体背光的暗影,既然背光的暗影就不能再比喻为光的箭矢,这显然是相悖的,比喻要有合理性,否则就没有规矩了,这也是很多朦胧诗让人看不懂的原因之一,就是比喻的过于随意,不遵从内在的合理性造成的。继而“犹如一条银色的鱼”也是失败的修辞,把雪豹的“影子”比喻为“光的箭矢”本来就不合理,除了前面说的,还有雪中的雪豹颜色如果是“光”的颜色,那么就会融入雪色中根本无法区分,而把雪豹的敏捷比喻为银色的“鱼”,也是很牵强,并且降低了雪豹的敏捷度,再放大点看,就像在说“雪豹奔跑的速度像龟”,见鬼,修辞出现了反作用,毕竟现实中敏捷度次于雪豹的熊都能抓鱼,形容雪豹的速度快用鱼来表现合适吗?显然这也是败笔,不过读者没有发现,是习惯自己被作者牵着跑造成的,毕竟谁也不会看电影是为了找穿帮镜头而花钱的,那样多无趣,所以读者被牵着鼻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作为同样为作者的评论者,这个穿帮镜头肯定要指出来,因为太明显了。此时回头看第一句,吉狄马加写雪豹并没有抓住它的特点来写,仅仅出现的毛色还是他想象出来的,压根没有写出雪豹半点真实的威猛样貌来,第二句写雪豹敏捷,也是弄巧成拙,反而将雪豹的敏捷度调成慢速了。所以第一句既没有写出雪豹“慢”中的样貌,第二句也没有写出雪豹“快”的身形,这就是败笔,不过就是在字数多上占点优势而已,只能说粗线条地小孩用尿在地上画画式地完成了雪豹的构图要求,如果这能成为经典,小孩的鸡鸡就会成为器官买卖的新需求。比喻是需要想象力的,恰当的比喻也需要作者具备缜密的心思,从这一句看吉狄马加的想象力还局限在前人用烂了的意象,缺乏个人独特的灵光乍现的顿悟,所以我不期待这种能力出巨制出惊世作品,基础太差。) 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 守望孤独,穿越了所有的时空 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 (这首诗明里是献给乔治夏勒,其实真正的创作动因还是把自己比作雪豹,试想吉狄马加与乔治夏勒是亲人吗是好友吗,乔治夏勒是诗人吗?吉狄马加是动物学家吗?如果这些都不是,那么激发吉狄马加的“献给”就不诚实,而像很多诗人都习惯自比摩西、基督一样,实实在在地激发了吉狄马加创作雪豹长诗,最核心的动力就来自自我感觉是一只雪豹而已,不过借乔治夏勒遮掩一下。这本身无可厚非,只要作品过硬,你献给谁都是一份大礼,反之就是不尊重了,既不尊重赠予的对象,也不尊重诗神。“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守望孤独”的出现应该在之前有伏笔,那么再回头看前两句,除了“雪豹”这个概念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孤独”,这两句的描写有“孤独”的笔触吗?没有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就是结构上的脱节,是一首诗整体构思的不严谨,诗歌的建筑美不单是整体上的,细节的铆合度牢固度也是考核检测的标准。诗歌的精神高度肯定是建立在诗歌的物质基础上的,不可能凭空产生,作者就是通过字词这些物质搭建出引导渠道的结构,逐步将读者带入精神高度的,如果管道的设计错误,读者在中途可能会坠亡可能会迷失方向也会被带入歧途,在诗境中失去诗境。“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是有诗性的,可惜这一句很“孤独”,比雪豹还要孤独。我倒是觉得如果吉狄马加开篇就从“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入手展开对雪豹的描写,或许更有效。不过我又不抱幻想 ,因为吉狄马加诗歌的跳跃有很多杂音乱象,既不紧扣中心又容易发散到不着边际,忘记了“回归”、“收心”的处理。) 我守卫在这里—— 在这个至高无上的疆域 毫无疑问,高贵的血统 已经被祖先的谱系证明 (大而空的抒情诗有这个通识,就是你看不出毛病,但也看不到精彩,说到诗性似乎也有一点,具体到哪一点有诗性,也浑然不知躲在哪。其实这种诗就是只有诗的外包装,里面没有实物。不论吉狄马加想要写雪豹,还是要写乔治夏勒还是要写自己,通篇看下来,你会看到他写的点很多,几乎面面俱到,但是回想这首诗时却没有一个点有印象,这其实就是平庸的表现。吉狄马加的诗会让不明就里的读者产生错觉,只要有人有组织有规模有意识地吹捧,他们就会觉得吉狄马加的诗的意境仿佛置身在天堂一般,那种落笔必提及疆域、血统、守卫的词汇,确实在中式教育里会产生这种通识惯性。诗歌要走下神坛,这种造神式的祭祀式的文本样式早就应该被丢弃了。或者你就专门给那种祭祀活动贡献稿件,不要出现在民间,因为民间写作的立场在地上在身边在身上在感觉在细节上。) 我的诞生—— 是白雪千年孕育的奇迹 我的死亡—— 是白雪轮回永恒的寂静 (讲好听些,这有点像绘画里的泼墨大写意,洋洋洒洒海阔天空,讲不好听的这就是故弄玄虚,如果是首创还有一定的探索价值存世价值研究价值,但这种文风有些烂大街,而且并没有多少艺术性。抒情诗的抒情也应该有出处,就像山泉水,总得有个源头,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哪是哪滑出来的。“我的诞生——是白雪千年孕育的奇迹”,这是在编神话故事,与其说是写雪豹诞生是个奇迹,不如说吉狄马加诞生是个奇迹,更容易接近这首诗想要传达出来的深层意思,就是捅破伪装层之后的真实意图。不管是写雪豹还是写乔治夏勒还是写吉狄马加自己,你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地上一句天上一句,写作目的在哪里?是要拔高写作对象吗?那么这种漫无边际地神话鬼话一通下来,你确定已经将这些写作对象拔高了吗?如果乔治夏勒和吉狄马加是那种史诗级的格萨尔王式的人物,这种抒情还能够匹配,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你就这么海吹合适吗?乔治夏勒和吉狄马加相对于格萨尔王,和大街上的素人有什么区别?起码吉狄马加诗歌这个水平就是凡夫俗子的。“我的死亡——是白雪轮回永恒的寂静”这种造句式的堆砌,都是为了给长诗凑整的无用功,越多越证明写作水平的平庸。换个角度看这种诗歌创作,是机器人可以代替的机械式的写作方式,身为诗人,肯定要写那种机器无法取代的作品,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因为这种写作没有任何价值了,机器人一天能写几万首,要你吉狄马加栽葱?) 因为我的名字的含义: 我隐藏在雾和霭的最深处 我穿行于生命意识中的 另一个边缘 我的眼睛底部 绽放着呼吸的星光 我思想的珍珠 凝聚成黎明的水滴 (写的是“名字的含义”,但是却绕开这个释义展开,虽然这也是一种手法,但是最终必须要回归到含义上才对,而吉狄马加是绕着绕着不知道把自己绕哪去了,而读者往往就觉得吉狄马加这样写很高级,其实是鼻子被吉狄马加牵着转圈转晕了而已。吉狄马加一会让雪豹“隐藏”一会“穿行”一会“眼放光芒”,但是都没有雪豹这种特殊生物的特质,你换成任何活物都可以用上,那么请问这有什么意义?在诗歌中篇幅有限的空间里,抒情也要有一个核心吧?又不是小说空间,容得下东扯西拉错综复杂。这一句的无价值就体现在写雪豹的文字用在其他活物上也不违和,就像写长江的文字,用在黄河用在亚马逊河都行,那么这句话有什么活着的意义,如果我是编辑,肯定拉出去当场枪毙掉,如果你有好看的一面,那就是死得好看,大快人心。) 我不是一段经文 刚开始的那个部分 我的声音是群山 战胜时间的沉默 我不属于语言在天空 悬垂着的文字 我仅仅是一道光 留下闪闪发亮的纹路 (“我不是一段经文刚开始的那个部分”这句确实在一瞬间给人一种神圣的错觉,你会觉得这样写很高级甚至具有了神性的光芒,但很可惜的是这只是“经文”一词带给我们的认知错觉,就像我们看到王冠一词就会产生高贵威严看到黄金一词就会兴奋一样,虽然撇开“经文”后这一整句确实有一种饱含诗技感,但是一个句子再好也要看它与整首诗的意境是否珠联璧合,所以很可惜,这一句的优点仅仅属于这一句,如果有的话。就像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也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好,不过还是佛经里的一句话,而吉狄马加这句如果是摘抄来的或者模仿来的,也完全有可能,因为这种句式被推到前台过。“我的声音是群山战胜时间的沉默”这种造句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是文字游戏,有修辞但无意义,我就是这么个看法,都是凌空高蹈不沾地气的故作高深。“我不属于语言在天空/悬垂着的文字/我仅仅是一道光/留下闪闪发亮的纹路/”,我承认这种句式有诗性,但是这种诗性是离开字词就踪影全无的诗性,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真正的诗性,自身不带诗性的属性,或者说它所具有的诗性很牵强,主要是没有根系没有源头,完全是靠随手一扔出去的字词产生的附着其上的诗性。不过很多诗人喜欢钻研这种诗歌创作手法,这些人,应该接受中国顶尖口语诗的洗礼皈依方得正法,他们对这种创作方法的坚守和执着就像迷信,被鬼迷住了。) 我忠诚诺言 不会被背叛的词语书写 我永远活在 虚无编织的界限之外 我不会选择离开 即便雪山已经死亡 (从这一段看,吉狄马加写的肯定就不是雪豹,也不是乔治夏勒,而就是他自己。雪豹只是一个喻体,乔治夏勒只是一个遮罩层,吉狄马加才是垂帘后面的真雪豹。因为动物学家乔治夏勒不需要用忠诚、背叛来表现,只有身处高位的吉狄马加才需要这种宣誓一般的表态。所以在确定了雪豹即吉狄马加之后,雪山就可以作为诗坛的喻体,那么吉狄马加就是自比一只在雪山一般的诗坛里的孤独的雪豹诗人,虽然身处高位,但仍然有一种“活在虚无编织的界限之外”的感觉,而“我不会选择离开即便雪山已经死亡”如果理解为“即使雪山一样的诗坛已经死亡没有了生气,吉狄马加也不会选择离开”,毕竟高官厚禄是比诗歌本身更直接地带给他功成名就愉悦感的,就很贴切。在他看来,诗写得好不好,并不是头等大事,因为他知道诗坛死气沉沉的原因,他如果要改变,可能最关键的是把自己撕碎了,“我不会选择离开”,“我不是一段经文刚开始的那个部分”,看来他有把假诗经写完的雄心壮志。) 应诗友要求选了他认为吉狄马加最好的作品品读,第一部分已经品读完,后面还有16段,大致都是一个套路出来的文本,品读没什么意义,放弃。我不会制造一个新概念去解析诗歌旧概念,就是尽量展现阅读第一感,口语化表述,可能习惯了诗歌术语概念的人看着别扭,但是我若用术语和概念来还原第一感,我也会别扭。诗歌讲究流动性,评价也讲流动性,咬文嚼字就会破坏流动性。
附上诗友对批判吉狄马加其他诗歌作品的回帖:
新泽飞翔:赞同评论所说“没有实质的思想内容”或者这就是作者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品 身后眼前:赞同楼主的点评。其实现在这些所谓的名诗人,尤其是官僚名诗人,现在基本都是不值一提。他们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主题先行”时代,全是空话,套话,陈词滥调。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的“老干体”。
幸运的是现在是自媒体时代。这些官僚名诗人是无法再吸引真正的诗人的眼球的。他们总归是历史的尘埃。
新诗的“主流”,真正的好诗现在都在“自媒体”里面。
现在不出名的诗人高手不少,中诗网,世界诗歌网里面就有不少真正的高手。只是现在大众还没有认识到而已。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