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郑立 于 2016-10-28 14:40 编辑
笺注白马山 文/(重庆武隆)郑立
黔蜀门屏
一条古驿道,被白马山揣进了怀里。 一块青石碑,被白马山握进了掌心。 在白马山大沙河的分水岭古驿道边,有一块高2米,宽0.8米,厚0.2米,刻写着“黔蜀门屏”的石碑。碑中大字长约0.5米,宽约0.3米,笔锋清丽,伫立在武隆县志的彩页,端肃遒劲。 从“光绪壬寅岁季夏月中浣谷旦”伊始,这块石碑消解两千年的蜀黔边界之争、商道之争。风霜雨雪,在古驿道上,跌跌撞撞。石碑,安然无恙。 从“知贵州遵义府安州事蜀东郎承谟谨识并字”发轫,这块心碑竖起了一百年来边地和谐的大纛。酸甜苦辣,在白马山上,起起伏伏。心碑,葱茏翠绿。 在传说里,一块百斤重的石头,从武隆道真的县衙同时出发,在两地英雄的脊背上,在两地边民的幺喊里,狼奔虎跃,相会在了分水岭。 在相会之处,郎承谟立碑刻字。一块青石碑,便站成了“黔蜀门屏”。 在石碑上,我企图还原时光斑驳的长短,那些受之于心的过去,那些持之于身的未来,比我的猜想更深沉,比我的狐疑更干净。 一块青石碑,成了过去的殇碑,成了未来的丰碑,成了民心之上的大碑。 黄莺大峡谷
萌芽在乌江的记忆,我曾经的一闪念,放纵在无垠的红尘。 黄莺大峡谷,千山万壑,从红尘中走到了红尘外。石掌之上,人掌之上,彼此的纹印,没有相同的暗记,尖叫的时间,泾渭分明。 前边石帘散开,可以千丈。后边石缝围来,也可盈尺。瀑腾鸟跃,心门敞亮,十五里深涧,是我初心的婉转。 石头的故事,雨磨在浪淘的分寸之上。 人间的恩怨,芽藏在花开的纤毫之上。 亿万年,千百年,默不作声,纠结在我愁肠百转的唏嘘。石头的脸谱,是我一点即透的暗语。 在峡门与峡门之间,佛光如烛。在锁拦与锁拦之间,阳光似箭。清流与绿荫的幻象,让我看清了,水绕峰回的妩媚。 在我的记忆里,留了一扇门。 在我的灵魂中,留了一条缝。 我在门缝之间,看清我真身的苦行。
黄柏淌
淌流的,是王子湖的清泪。我的心绪,已经盘根错节。 在白马山之巅,在重庆海拔一千四百米的高山之湖,一只山鹰,用淡墨之钉,在我理想的高处,悬挂三十万亩原始森林,铺展一幅大美人间的磅礴秋韵。 在大草甸上,我盘膝而坐,秋虫催赶鎏金的时光,浅草如毡。前边是静谧的王子湖,后边是万亩起伏的杜鹃林。耳边的风声纵横,杜鹃林鸟鸣如瀑。 与一棵孤独的老杉对视,分辨各自的梦境,说出各自的真心:生我在王子湖边,葬我在杜鹃林前。 谁种下了这一棵老杉?种下了王子湖的孤独,种下了白马山的伤感,种下了传说里的一句祝福:爱是一千的孤独,爱了一万年也不后悔。 秋阳在蓝天上,追牧我晶亮的白云。 风吹湖面,树影粼粼。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得容我好好想一想,美丽易碎。 望仙崖
一朵凝望的云,在乌江之上,拴着鸟的翅膀。 在神仙的瞭望里,我看山。在神仙的耳语里,我听崖。 把仙风道骨的心思拉了回来,阳光趴在我的指尖,心事如花。 神仙的故事触及到了庸常。七仙女,牛郎,王母娘娘……添上一个白马山王子也不算多,让王母娘娘的金钗,划出了一道乌江。 盈走在神话的乌江,在望仙崖说我的姓氏,拉纤的水手陷入崖壁的丹霞。 闪烁在峡谷里的号子,一声声,在时间里结茧,向着我的祖先,一个个请安。 我应该知道,刻在石头上的文化很苍白,刻在思想上的文化很锋利,刻在灵魂上的文化很辛辣……文化是针针见血的爻辞。 对于我,望仙崖凸凹在乌江的永恒。 对于望仙崖,我无语的心情扦插时间的秘语,清澈,透明。 我望断一片天光,抱着跌宕的隐痛,为乌江无言的美丽,守灵。
神龙湖
山虎关,已锁不住我一湖的真心。 在时间的空白,神龙湖从白马山划向乌江,绽放我心头的美丽。 目清眉秀的山水,渗透在草根上的心情,在民歌上,铿锵,妖娆。 多年以前,大胡子土匪也没能惊动我简单的信仰,一把热血弯刀,斩断月光。 多年以后,我满腹经纶的惆怅,在神龙湖上,垂钓月光的弦音。 我坐在弯刀上的梦境,比着太阳高度,看我五十年来的道路。在岁月的原点上,在山虎关水库上,红旗飘飘。 我的倾听不容折叠,颂歌与日月同辉。 我的颂歌不容拆换,倾听与山水同在。 神龙湖,在白马山的名片上,咀嚼星光。
城门洞
风,嘶哑在耳边,还原一种述说。 乌江,折戟在峡谷,回归一个传说。 白马山耸了耸眉毛,过境的秋天便冷了下来,托举黄叶纷纷的山脊。 在城门洞沧桑的缝隙,我捡拾白马山的断简。 在时间的藤蔓,我捕风捉影。在青石板上,我穿峡过帐。 乌江古道,絮叨着扯船的往事,盐茶入味。 土家腊肉、仡佬油茶、苗家甜酒……颗粒饱满的深邃,在舌尖上落花。在遗迹的文字,我寻踪闻香的亡灵。 立壁若城,城门若洞,一山洞开,婉若仙境。犹如时间的深义,历史的底片。 在城门与洞之间,神出鬼没的响马,出渝入黔的马帮,羁旅风尘的烛火,斗转星移。 一阵风来,深涧如砥。万鸟飞尽,隐没了留白。 一阵雨去,高峡若霓。万径雾罩,泯灭了阒寂。 紧随花开花落的命运,我在城门洞,缘木求鱼。。
凉水老寨
幺店子,不再是一句黑话,煨暖寒夜的一坑火炉,爽透毒日的一碗凉水。 从记忆里淘出,还原在当下。老寨门站出了好远,蹲在崖头的瞭望亭,看破了红尘。 一排排木板房呢?我找不到一廊一柱、一砖一瓦的匪气。土匪鸡,在凉水老寨的掌故里,热气腾腾。 连片的荷塘,连片的花田,连片的竹影……打马而过的余音,风凉,雨润。 忽然想起丰乳肥臀的压寨夫人,想起秋阳下婀婀娜娜的金菊花,在时间的扇面,笑不露齿。 我无法淡定,喝酒的大碗也在,吃肉的大碗也在,烤脸的篝火也在,但是家家无匪。 匪山、匪人、匪事,全部陷入了炭火的封尘,滑入了凉水老寨的根底,匍匐在白马山的梦境,翻山越岭。 一场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匪事,忍受了我不期而遇的悱恻。
万家营
大白崖,漂白了白马山的雄奇。 长途河,问津了白马山的盛典。 一匹狂放的白马,在重庆的肺腑,踏出旖旎的尘埃。 一个精彩的停顿,在解放的硝烟,点出历史的童眸。 万家营?万家银?喜新厌旧的名号,在官家和民间的岔道上,山寒水廋。 左边九倒拐。右边九倒拐。十八个“之”字拐,在川湘公路上,芝麻开花。 万家营,万营,我在家的词句里,烟缭雾绕,各怀其辞。 万家银,万银,我在家的瞭望里,金山银水,各就其位。 撩拨我家的眺望,在浅灰和深黛之间,往复我万家营梦呓的发簪。 远处,一滴乌江的热望,舒卷在银巷口。 近处,我心上的金巷口,席卷在大西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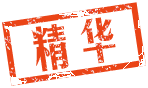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