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郑立 于 2018-11-3 09:48 编辑
归隐在我骨头的村庄
1
湿漉漉的井,湿漉漉的深;湿漉漉的手,湿漉漉的光;湿漉漉的绳,湿漉漉的桶…… 老井,村庄晨曦和暮色的一脉。透过生命之夜的水,如花似玉,清纯甘甜。 一颗湿漉漉的心和一尾在井边站立的鱼,所有的念想,披着春色,垂于山岗之上,迎着时光的回响。喝过了老井的水,我的骨头蓄积着三分寒气。 谁的一只布鞋遗落在了井边?高速公路劫掠了我的村庄。我就是那个被城市领走的人。 曾深陷在村庄的马嘶驴叫、鸡鸣犬吠,还睁圆梦游的眼睛。曾滚涌在村庄的猪哼羊咩、鸠咕雀噪,还皲裂着渴望的嗓子。我的老井,枯瘦如柴,青苔入眼。 我从不薄情寡义,心系着老井的根须。三分寒气,一分给了昨天的恩赐,一分给了今天的抚慰,一分准备给我明天的猜想——叶落归根,归隐在我骨头的村庄? 雾霾时候,天空如井。磐石的黑缭绕在我的胸口,我听见老井喊我的声音。
2
怎么找不见呢?我骨头上的村庄,只有轻柔的风,与我一路耳语。玉米杆垛、高粱杆垛、麦草垛、稻草垛、柴草垛,都藏了。我就是那个爱玩捉迷藏的孩子。 看着我长大的人,藏进田垄的一隅,在一岁一枯荣的风里,还有他们无声的叹息。轻吻过我的竹林、果林、树林、藤蔓,依然站在房前屋后。 蓄满收获的草垛,晾晒渴望的草垛,搂紧温暖的草垛;藏过我梦想的草垛,藏过我甜笑的草垛,也藏过我委屈的草垛……都是我生命的章节。 那些一生追随我村庄的草垛,藏在哪里了?在村边,一口井、一口池塘、一条小溪已不给我暗示。柏树上独自嘀咕的斑鸠,也不递我眼神。残破的老墙,锈迹的铁锁,荒芜的小径都心照不宣地犹豫。 藏在哪里了?我的眼,掘地三尺。我的心,驰骋千里。 我的草垛,村庄的风语。在城市的画布上,面红耳赤。
3
秧苗拱泥时来。稻粒归仓时去。 一整个夏天都在我的瞩望里,飞针走线。 从衔泥筑巢,到剪云入牖,我读懂了什么是勤奋。 从雏燕鸣晓,到新燕凝秋,我读懂了什么是缘分。 盈盈的曼妙,绵绵的徘徊,淅淅的离愁,灵动在我的梦中,在我绿苔虚掩的房檐。 想弱弱地追问一句:我骨头上的村庄,归去了何处? 穿梭在梦境的思想、灵魂和信仰,牵动大地的呼吸,牵绊大山的心动,牵挂小河的涟漪,走在我村庄的夕阳里,噙着我感动的泪水。 仿佛我又听见响在村校老树杈上的钟声,看见在钟声里高翔的燕子,握住燕子划在心头的金线,以及金线勾勒的呢喃…… 我的梦里,每一只燕子都提着来去的灯盏,照亮我村庄的欢悦。我听清了我追赶的梦想,听清了我追赶梦想的脚步。我的沉默布满了神往。 麦粒一样饱满的心,稻粒一样深情的心,夏天一样厚实的心,因为一声燕语柔软了,因为声声燕语纯净了,那些触手可及的细节,丛生我孜孜不倦的怀想。 找到了暖心的柴火,找到了柴火上的炊烟,听见了炊烟幸福的呻吟,听见了无法诠释的心语,在春天的节气上,透明着我的梦想,也透明着村外银带一样奔入长江、奔向大海的乌江。 燕语入心,是我穷尽一生的渴望。
4
一入冬闲,地净场光。雪孕春晖,万物登场。 用犬吠印剧本,用牛哞录唱调,用鸡鸣说戏份。每一句插语,不讳贵贱。每一声打诨,不杂虚言。乡音的唱腔,老树的新枝。字正。腔圆。 锣鼓咚呛。唢呐咿呀。演绎巴人鬼神,祈愿幸福安康。也说《六月雪》,也唱《状元与乞丐》,也扮《打渔》和《采桑》……黄发垂髫,鹤发童颜,唱星移,说斗转。 村里人演给村里人的戏。主角、配角、观众,在台上台下,命运交替。在时间的间隙,是非分明。 舞龙是戏,舞狮是戏,人舞是戏中之戏。 台下说戏,台上唱戏,鬼神是戏中之戏。 自强不息,村戏的神。厚德载物,村戏的魂。落叶归根,村戏的鬼。 速度和节奏,言辞和信心,穿梭在村庄的传奇。 人来人往,人潮涌。在吹拉与弹唱里,你抖出一个亮飒飒的好收成。 春来冬去,春潮急。在低沉与高亢里,我喊出一个红朗朗的好年景。 千般柔情,也逃不出命运的开场与落幕。 万种蜜意,也逃不出人生的流泪与嘘唏。 人间有情,村戏不绝。人间有爱,村庄有根。
5
明火。旺火。文火。温火。火候在手上。 在一张一弛的捏拿里,酒甑里的曲香淌着庄稼的一腔热血,高粱、玉米、糯米蓄满一甑脱胎换骨的疼痛。 石隙流出的甘泉,土地长出的热望,人心涌出的凛冽,在一坛坛村酒的窖香里,古意如钩。 头酒,虎头如酣。千锤百炼的信念,在山野里吼喊了千年。 尾酒,豹劲如鞭。穿云破雾的翘盼,在旷野里逡巡了千年。 中间的酒,是缠缠绵绵、绵绵缠缠的花酒啊,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之间,沉醉千年。 脸似鸡公,步如羊瘸,声似马奔,在酒碗里,每一个醉汉都是我最心疼的人,每一次畅游星汉的想象,都在我平步青云的憧憬。 在红红火火的火塘边,一坛村酒就是一条上天入地的大路。 在朝云暮雨的酣梦里,一坛村酒就是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路。 在古诗里,我扶起了红红火火的火塘。 在酒坛里,我扶起了踉踉跄跄的村庄。 在城市里,我扶起了浑浑噩噩的酒杯。 才发现,我身后的这个冬天,句句炽热,字字温暖。 才发现,我眼前的这个春天,花讯如潮,金光闪闪。
6
袒露冬天的雪肤,透闪锋利的寒光,刺入我夏天的骨头。 金色的沙粒从泉眼里涌出,晶亮的气泡从泉眼里涌出。那些沉寂千百年的冷,从泉眼里涌出。我不老的记忆,也从泉眼里涌出……冷泉,村庄的冷火焰。 离开村庄的人,带不走冷泉。离不开村庄的人,喊不走冷泉。随风而过的猪牛羊、鸡鸭鹅,唤不动冷泉。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也都冷泉上的过眼云烟。 汩汩流淌的清冷,幽幽暗潜的伤感,都起伏在村庄的炊烟上。尔或,徘徊在泉边的鸟,会叫几声冷清。从冷泉边走过,也有了鸟的冲动,离开村庄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想张一张嘴。 一种静谧的典雅,与天空、太阳、月亮、星辰心心相印。大地的辽阔,苍穹的坦荡,昼与夜的深远,齐聚在一眼冷泉。甘冽,不是空灵的童话。冷清,不是无根的传说。冬温夏冷,寒气如刀,都是人心的错觉。 几丈外的草木,几里外的小溪,几十里外的大河,几百里外的大江,几千里外的大海,也对此保持沉默。所有的念想,在淡淡的炊烟里,扶起一个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人。 千百年的冷。淡淡的乡愁。让我心净。让我心静。听花开的声音,听梦想的声音,听幸福声音,那些牵挂我的人,比如我的母亲,都住在这些声音里。 冷泉,归隐在我骨头的村庄,还是不是一只不眠之眼?
【作者简介:郑立,男,60后,重庆武隆区人,重庆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星星诗刊》《散文诗》《诗林》《诗歌月刊》等,与人合著《等一个秋天》。地址:重庆市武隆区卫生计生委;邮编:408500;qq:491648638;电话:139835807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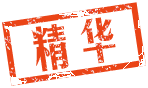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