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雨夜人鱼 于 2020-9-15 06:56 编辑
栏目主持:赵佼
“新性灵”之翻译“妙合论” ——龚刚教授访谈
赵佼:中国传统诗学是当代诗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何转化古韵十足的术语,让人望而却步。文学翻译“妙合论”则是化合中西、古今的成功例子。龚教授认为理论创新源于深广的知识储备及实践经验(创作及批评经验),后者较被忽视。“妙合论”源于新性灵诗歌创作(翻译)及批评实践,这当属其一大特点。 龚刚教授:新性灵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崇尚顿悟和哲性;作为批评倾向,崇尚融汇贯通基础上的妙悟。长久的体验,瞬间的触动,冷静而内含哲性的抒情,大抵就是我所谓新性灵主义诗风。而李贽、金圣叹的性灵化批评,加上会通古今中西文白雅俗的知识视野和美学参悟,即是我所谓新性灵主义批评。 “妙合论”是新性灵主义( 见《七剑诗选》前言,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 在译论和译艺上的体现。文学翻译亦须闪电般的照亮与灵感。所谓神会,是领会其精神,不是不要形式。若无神会,难得其真。神形兼备才是妙合之译。神会是态度,是过程,神形兼备是结果。从认识论高度而言,神会是凝神观照,默体其真,近于伽达默尔所谓视野融合。 赵佼:龚教授认为“金圣叹式的文学评点是一种与机械主义作品分析相对立的性灵化批评,融入了作者的性灵与妙悟,并擅长以隐喻思维与诗化的语言对名著的美学特征予以评说,短短数语,即可传其神,摄其魂。”《文学翻译当求妙合》一文从篇幅上讲并非鸿篇巨制,却字字珠玑,这样的撰文方式是否可以看做是评点体在现当代学术语境下的一种尝试? 龚刚教授:我在《科学思维的局限性与诗话批评的复兴》一文以钱锺书对神秘主义思维的辩护为切入点,探讨艺术与科学以及审美批评与科学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肯定“美术之知”的价值,提出复兴诗话体的构想,主张文学批评不应排斥性灵与妙悟,而应将理论融入想象和直觉。 诗话是一种“片段性”的文学批评形态,它为唐以来历代学人所习用,但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已逐渐绝迹。和札记体著述一样,诗话也往往是若干没有直接关联或逻辑联系的知识片段的连缀,因此,诗话也可以说是一种札记体的文学批评形态。其具体特征为结构比较松散,内容比较驳杂,行文也比较散漫,作者的种种玄思妙想、审美感悟以至美学趣味、生活情趣也因而得以较本真地呈现。这也就是诗话何以更贴近人的生命体验、更贴近所考察作品、更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原因。钱锺书在肯定“片段思想”的价值时,对诗话的特征作了点评,他说: “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由此可见,诗话的日趋绝迹,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学人渐重理论系统和周密思想的研究取向在文艺研究领域的直接体现。 那么,诗话这种文学批评形态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和必要呢? 我对此持肯定的态度。纵观20世纪以来的文艺研究,有计划、有步骤、逻辑严密的科学主义研究模式日益占据主流地位。它固然使我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更周到、更全面,但由于科学化研究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排斥感性与偶然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如诗话体以及评点体所显示出的即兴而发或有感而发的偶发性与性灵化特征便受到抑制。这一方面使当前的文艺研究由于过分追求科学主义规范而显露出程式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使崇尚兴会妙悟的文学批评方式得不到相应的重视。 面对评点体在现代学术语境下的尝试与成功,我对诗话体的复兴有了更充足的信心。不过,由于传统“诗话”“词话”的研究对象是古诗词,表达形式一般是文言文,这就给诗话体在当代语境下的“复兴”提出了一个难题: 如何以白话文的形式对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及相关背景(范围广于旧时所说的“掌故”) 作出片言居要、富于灵心妙悟的评价,且又能在统一的风格下连缀成篇? 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去尝试、探索的问题。尤须强调的是,对“诗话”批评的复兴不应作胶柱鼓瑟的理解,它既不是文学研究形态上的复古,也不单纯是诗话体的现代转化。事实上,笔者强调“诗话”批评的复兴,并欣然于评点体的重现,最根本的着眼点并非诗话或评点这两类体式能否“续命”,而是更重兴会妙悟和具体鉴赏的文艺研究模式在现代中国学术演变之大趋势下的命运和前景。
赵佼:龚教授谈到“海子陷阱”,究竟什么是“海子陷阱”呢?这是否也印证了“诗话”批评或兴会妙悟式的文艺研究模式在现当代学术语境的重要性呢? 龚刚教授:长诗与诗的本质相冲突。史诗、长篇叙事诗,以及《浮士德》式的诗剧,就像散文诗,本质上是跨文类。Burns is better than Chaucer in the name of poetry。后者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明明就是tales narrated in the poetic form。屈原的《离骚》、杜甫的《咏怀五百字》、李白的《蜀道难》、白居易的《长恨歌》,够长了,也不必再长,不能再长。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孤篇冠唐,才多少字?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穆旦的《诗八章》,算长了,也不必再长,不能再长。海子尝试写长诗《太阳·七部书》,结果失败了。当今有什么成功的长诗吗?好像没有。跨文类的不算。很多诗人没搞明白,长诗不等于大诗,包括海子。大诗就是以精短诗行涵盖一种精神、一个时代甚至一部历史,如顾城的《一代人》。对长诗的执迷,可以称为海子陷阱,译成英文是 Haizi’s trap。 很多长诗其实是短诗的组合。诗性语言源于灵感、兴会,而两者不常有,更难持续。 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Paul Valery)说:“一百次产生灵感的瞬间也不过构成一首长诗。因为长诗是一种延续性的发展,如同随时间变化的容貌,纯自然的诗情只是在心灵中产生的庞杂的形象和声音的意外相会。” 瓦氏的看法从反面印证了长诗(几百行或以上)不合诗性,因为,没有产生灵感的瞬间,不可能有诗。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所谓“诗于沉静中回味得之”的前提是,要有这个被闪电抓住的瞬间。而要把上百次闪电以逻辑贯穿之,是几乎不可能的。当年柯勒律治写长诗Kublakhan(《忽必烈汗》),思路被打断,闪电消失,诗也就写不下去了。 华兹华斯的《序曲》为自传长诗,其性质是长篇散文诗,也不是纯诗。读此作,主要看故事、经历及其人生哲学,其中也有警策之句,但就诗艺而言,不如其短短一首《水仙花》(The Daffodils),甚至更短的《我心雀跃》(My Heart Leaps up):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A rainbow in the sky: So was it when my life began; So is it now I am a man; So be it when I shall grow old, Or let me die!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And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
试译作:
仰观霓虹 我心雀跃 幼年如是 壮年如是 垂暮之日 亦当如是 若不欣然 与死何异 稚子为父 人生如初 敬天之心 一以贯之
短短数行道尽浪漫主义自然哲学精义和生之喜悦、死之坦然,语言大巧若拙,堪称大诗。 赵佼:《从感性的思乡到哲性的乡愁—论台湾离散诗人的三重乡愁》一文中龚教授首提“哲性乡愁”,对“真”的追问,是诗与哲的应有之义,“妙合论”里有“神会是凝神关照,默体其真”,诗与哲的关系对诗歌翻译有怎样的影响呢? 龚刚教授:《妙合》一文中我谈到诗与哲学都以创造性使用语法的方式表达特殊意涵,如美国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的诗歌喜欢违反语法常规使用大写。俄国形式主义又称语言诗学,主张突破常规表达与日常语言,令人发现习焉不察的常见事物的本真面目。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奇异化的文学语言的功能就是让石头成为石头。雅各布森则进一步强调陌生化效果。Robbins 的诗观也是什、雅一脉,他所谓fucking around with the syntax,可译为操弄句法。从中西诗歌与哲学的大量语用实例可见,个性化或诗化的表达常常有意突破语法常规。Garry认为,如果你是rap artist,“Then all rules go out the door,and you are acceptable。”狄金森的诗歌极具个性,又富于神秘体验,以难译著称。译其诗,须有闪电般的照亮与灵感,方能达妙合之境。 赵佼:龚教授谈到“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精神,其次是思维方式 (出位之思),最后才是方法(影响研究、平行分析、双向阐发等)”,您所创立的“新性灵诗学”及文学翻译“妙合论”是怎样体现“出位之思”的呢? 龚刚教授: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才是中华文明演进之道。有一位西方学者说得好,中国不仅是国家,也是一种文明。我在《如何创造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形式?——回顾 1940 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A Review of the Debate over the National Form in 1940s: How to Create a National Form for Chinese New Literature?”)一文中主张以比较文学思维推进本土研究与理论创新。质言之,比较文学思维的根本内涵是“出位之思”。所谓“出位之思”,即是不为学科、文化、语言藩篱所缚的思考方式与探索精神。 既然比较文学思维的根本内涵是“出位之思”,那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本土文学、本土文化就应当以不为学科、文化、语言藩篱所缚。我所创立的新性灵主义诗学即是在中西诗学对话的背景下,发展了明清性灵派的诗学思想。不提刘勰、福柯,而刘勰、福柯自在其中。 新性灵主义诗观及批评观孕育于我的研究课题《徐志摩文艺思想研究》和七剑诗派在文学微信群“澳门晒诗码头”的创作实践,是自然生长的,而非标新立异的凭空虚构。拙文《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与《新性灵主义诗观》已初步搭建起新性灵主义的理论框架。明清性灵派崇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自由,究其实质,是以《礼记·乐记》所谓感于物而形于声的“心物感应说”为思想根源,以人的自然本性、生命意识为核心,以佛教“心性”学说为推动,强调文艺创作的个性特征、抒情特征,追求神韵灵趣的自然流露。性灵派有多个译法,其中以音译加意译的HsinglingSchool最能彰显中国理论话语。因此,新性灵主义可相应地译为 Neo-Hsinglingism。 新性灵主义诗学源于创作、批评、翻译实践的心得,包括四个方面: 1) 诗歌本体论。其要义为:诗性智慧,瞬间照亮; 2) 诗歌创作论。其要义为:一跃而起,轻轻落下; 3) 诗歌批评观。其要义为:灵心慧悟,片言居要; 4) 诗歌翻译观。其要义为:神与意会,妙合无垠。 西人有格言曰:“Roads in the mountains teach you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in life.What seems like an end is very often just a bend”,如以陆游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译,可称妙合。好的翻译必是比较文化家,优秀的文学翻译是天然的比较文学家。形象点说,优秀的译者是语言演奏家,尽显原著的格调与神理,如风行云起,弦随意动,妙合无垠。欲达此境,须精通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且佐以悟性、灵感。译理通诗理。 赵佼:据悉龚教授主编的《新性灵主义诗选》即将出版,与《七剑诗选》相比,《新性灵诗选》在阵容上更强大,汇集当代诗人名家,很期待! 龚刚教授:感谢各位诗友!新性灵主义诗学的建构是以“七剑”(七位诗人) 的创作为立足点而建立的,追求既有鲜明个性,又心系苍生、民族和天下的大侠精神。新性灵派乃非派之派,妙用随心,也不必自缚手脚,画地为牢。新性灵主义创作观是一种崇尚各随己性、以瞬间感悟照亮生命的诗学信念,并非教条。换言之,新性灵主义创作观是机动灵活的、强调个性的、主张先天与后天相结合的,而非机械的、呆板的、一成不变的。因此,任何有意于此的作者均可从中受益。 参考文献: 龚刚.从译之妙合到审美启蒙[C]复旦谈译录(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 2020. 龚刚.从感性的思乡到哲性的乡愁—论台湾离散诗人额三重乡愁[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1). 龚刚.李磊《七剑诗选》[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 龚刚.科学思维的局限性与“诗话”批评的复兴[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1). 张叉 龚刚.以比较文学思维推进本土研究与理论创新[J]外国语文研究,2019(6). 龚刚.新性灵主义诗学导论[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9(6).
龚刚, 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学术总监、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扬州大学访问讲座教授(Guest Chair Professor),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客座教授,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委(2019-2023),《澳门人文学刊》主编,《外国文学研究》编委,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作家出版社等出版《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现代性伦理叙事研究》、《中西文学轻批评》与《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乘兴集》、《七剑诗选》等著作及诗文集,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中华文史论丛》、《伦理学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A & HCI收录)、《人文中国学报》(香港)与《钱锺书诗文丛说》(台湾)等学刊或论文集发表诸多论文,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伦理叙事学、比较诗学研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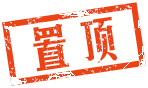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